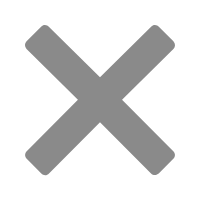-
棺生子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第 1 章节
1
“咚咚”“咚咚”
灵堂前,停着一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棺材板。
不同的是,棺材里隐隐传来敲击声。
可守灵的人不在,没人能听到。
过了好半天,棺材里才没再发出其他诡异的动静。
可就在下一秒,里面突然传出一道凄惨的叫声,划破了黑夜的寂静。
与之同时出现的,是另一道嘹亮的啼哭。
生死交汇。
在灵堂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可怖。
大门砰的一声被推开,一个披着外套的老人身影站在门口。
她带些跌撞的跑来,左看右看,都打不开那口已经钉死的棺材。
没办法,只能找屋里拐角处的锤子,撬烂了棺材板。
棺盖被打开的一瞬间,一股尸臭混合着血腥味扑面而来。
老人用袖口挡住鼻子,使劲探着身子往里看。
「这…这…作孽啊…」
棺材里,除了已经死去多时的女人,还有她身下带着一团血污的婴孩。
那孩子全身青紫色,口鼻间仿佛还有些血水,眼看就倒灌着进了喉咙。
本来嘹亮的哭声此时也被噎得发不出来,小脸黑紫黑紫的,仿佛下一秒就背过气去了。
老人在棺旁踱步,内心挣扎。
按理说,棺生子是灾厄的象征,本该与母体同葬。
可眼下,这个小孩还有一丝生机,毕竟,孩子是无辜的……
狠了狠心,老人弯下腰,从棺材里把孩子抱出来。
见孩子险些没了气息,忍着恶心。
腾出一只手捏开他口鼻,自己将他嘴里的血水尽数吸了出来。
孩子的哭声再次响起,老人则扭过头,在一旁干呕着。
老人本想把孩子交还给这家人,但当孩子带着好奇,伸出软软的小手,捏住她指头的时候,老人心软了。
罢了,这户人家本来对媳妇就不好,更别指望能对棺生子好了。
她是村里的神婆,本是来参加出殡的,可现在,平白给自己领回去个孩子。
哄了哄孩子,看着他虽泛着青紫,但也已睡熟的脸,老人久违的露出了笑容。
紧了紧身上的外套,迎着风,老人抱着孩子,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。
2
十几年后……
我坐在院子里,无聊的用棍子戳蚂蚁玩。
本该是上学的年纪,可自从被老师针对后,我就不再去学校了。
奶奶疼我,不愿我去受罪,也就任由我在家里到处疯玩。
「臭小子,你奶呢?」
门口探进来个脑袋,贼眉鼠眼的问我。
我眯了眯眼,这人好像是村里猎户家的小子,仗着家里有枪有钱,从小就在孩子堆里称王称霸。
我没少被他欺负。
我没停下手里的棍子,径直戳在一只蚂蚁身上,将它压在棍子下,冲里屋努努嘴:「做饭…」
听到奶奶在家,那人好像松了口气,赶紧跑进来。
几步踏上我家院里的台阶,一跃而起,路过我头顶。
我被吓得缩了缩脖子,手一用力,棍子下的蚂蚁竟被我碾死了。
看着它身首异处的尸体,我轻轻捏起,在指尖用力撵了撵。
真是,不好意思啊……
「喻奶奶,你快去看看吧,我叔…我叔死了!」
我蹭地一声站起来,村口那个职业猎户——旺叔?
奶奶在围裙上擦擦手,忙不迭摘下围裙,持着根拐杖,跟他一起往外走。
走的时候,还不忘嘱咐我在家看家。
我又悻悻坐下,这些年,奶奶每次看事儿的时候,从来不让我出现在这种场合。
可是,她不让我去,我就不去吗?
他俩前脚一走,我后脚就跟上。
没几步就到了村口,这里已经围了一堆人。
奶奶拨开人群往前一看,赶紧又退了回去。
饶是她见过很多死人,也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手法。
那小子拽着奶奶的衣角,带着哭腔道。
「喻奶奶,你看,我叔,是被狼咬死的……」
确实,那残缺的尸体上,留下了很多深深浅浅的牙印,再加上被不规则撕扯走的肉,赫然是狼留下的没错。
但,为什么在山上出了事,却能被叼到村口来?甚至有些故意引人注意的样子……
难道这狼也成精了?
奶奶走上前,对着旺叔的身体转了几圈。
点点头。
「不错,确实是打猎时被狼咬死的。至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,旺子打猎狠,可能无意间伤了狼群,狼是群居动物,报复心极强,也通人性。这恐怕是对我们的警告啊……」
3
我不知道喻奶奶之前是干什么的,只是,这里的人都把她奉为神婆。
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,三言两语,就打消了人心头的恐惧。
而且还告诫人们,做事留一线。
我在人群后,自嘲着笑出声。
我生来坎坷,却从来没人想对我做事留一线。
奶奶冲那哭哭啼啼的媳妇说:「旺子家的,你也别太难过,这生死有命,以后就辛苦你了,把这俩娃带大……」
旺子媳妇点点头。
她也是个命苦的,小叔和弟媳生下儿子就死了,他俩养起了人家儿子不说,自己没两年又生了个姑娘。
这下,旺子死了,哪有收入去养两个娃?
可别人才不会管她,村里人嘛,惯会用明哲保身的手法。
奶奶给了旺子媳妇一点钱,让她抽个机会把旺子安葬了,就驱散了众人。
众人鸟兽状散开,露出了藏在人群后的我。
本来神色无常的奶奶看到我,一瞬间变了脸色。
忙走过来,一把提溜住我。
「不是让你看家吗?跟我来做甚,你这坏娃……」
奶奶揪着我的耳朵,带我回家。
「哎哟哎哟,疼!」
我叫喊着。
奶奶虽然拄拐,但腿却没什么事,是做给村里人看的。
她身子不错,甚至走起路来健步如飞,我都有点跟不上。
但我是高兴的,因为奶奶,可能是世上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。
躲过人群视线,奶奶松开了手,看着我道。
「泰娃子,以后,一定不能跟着奶奶出来了。村里人都不喜欢你,奶奶怕……」
我点点头,我又怎么不知道呢?
奶奶叹了口气,摸摸我的头顶。
「走吧,奶奶回屋给你蒸大馒头去……」
我跟上她,踩着奶奶的影子,一步步往家走。
4
如果说,旺叔的死大家都以为是个意外的话,那接下来发生的事,就说不清道不明了。
没过几天,又有人来寻奶奶了。
我对这种事见怪不怪,奶奶身份特殊,每天来找她的人都快踏破门槛了。
可来人说,让奶奶去水塘看看。
村里,又死人了。
我央着奶奶,说只远远的站着,不往前凑,让她带我一起出去。
奶奶拗不过我,只能答应。
我停在距水塘好远的槐树下,看着那边人头攒动。
这次死的,是惯会水性的贵哥。
贵哥家里祖祖辈辈都靠打渔为生,他本人更是离谱,有传说,他生下来就会凫水,哪有淹死的道理?
可贵哥,偏偏是被淹死的。
被发现的时候,尸体都不知道在水面漂了多久,四肢肥大,肿得像个假人。
奶奶走过去,看着死去多时,已被打捞上来的贵哥尸体,掩着口鼻说。
「谁发现的?」
人群里有人默默举手,往前走了几步。
「是我,喻奶奶。我路过水塘打水的时候,发现上面飘着个人,走近一看,没给我吓死……」
奶奶摆摆手,沉吟片刻。
「看来,阿贵死了有几天了……」
围在一起扎堆的村民开始了激烈的争执。
「不对啊,村里没人能比贵子水性好了,他咋会淹死?」
「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,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,他命不好啊…」
「老哥,你可不能这么说,想想那天旺子死的时候,大家不都也以为是意外么!」
「说起来,为什么这几天接二连三死了这么多人,难道……」
众人越说越离谱,连带着牙都跟着打颤。
奶奶清了清嗓子。
「水性好的人咋就不会失足淹死了?这…可能是因为最近汛期涨水,也可能是因为腿脚抽筋,跟闹鬼有什么关系?」
村里人一听奶奶说话了,那些忿忿不平正准备辩论的人们也都住嘴了。
奶奶依旧扮演着稀泥的角色。
就在人们准备散开的时候,人群里又冒出来一个声音。
「不对,那天,我看到贵子了!」
大家停下了脚步,侧目看着他。
5
贵子为方便打鱼,建了一支捕鱼小队,里面全是年轻的后生们。
那个说话的,恰恰是队里成员之一。
他说,那天他路过水塘的时候,正好看到贵子在河里捕鱼。
他跟贵子打招呼,可贵子就像没听到一样,一浪一浪的一股脑往水底钻。
他说,那天的贵子好像变得不一样了。
平时大家一起捕鱼的时候,他总是劝人们往浅水区捉,捉不到就算了,命重要。
可那天,贵子像疯了似的,一个猛子就扎进水底了。
他看贵子失了智,没敢多说,就往回走。
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他总觉得,那天水塘里的水草特别像——
女人的头发。
「啊!」有女人被他阴恻恻的一讲,吓得叫出了声。
众人向后看去。
女人惨白着脸,颤抖着说。
「前几天,我儿子不小心掉进水塘里了,被别人救上来时,身上只有水底的淤泥啊,哪有什么…水草…」
大家一回想,是啊,这片水塘根本没有水草!
那他看到的是……
听到女人这么说,刚才还说话的男人赶紧闭上了嘴,出于害怕,飞也似的跑走了。
路过我的时候,他放慢了脚步,满含怨恨的看了我一眼。
我有些纳闷,又不是我推的,看我作甚?
男人跑走了,我继续看过去。
奶奶脸色也发白了。
这是大概是时隔多年,她再次碰到的这种鬼怪之事。
奶奶佯装镇定:「事情还没查清楚,话也不能说这么满…闹不闹鬼的,只要不做亏心事,就不用怕鬼!」
大家嘀嘀咕咕不知道讨论着什么。
可笑,这个村里,真有人没做过亏心事吗?
我能感觉到,有一些人不断在回头看我,仿佛我就是那个带来灾厄的恶魔似的。
我从槐树墩上跳下来,低着头默默往回走。
不知奶奶说了什么,人群一下就散开了。
奶奶跟上我,看我表情不对,试图安抚我。
我摇了摇头,挥开奶奶准备盖在我头上的手,快跑了几步。
掩住嘴边即将溢出的笑意。
呀,这么快,就要被发现了吗?
6
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平息的时候,又传来了噩耗。
村里林老师一家,被灭门了。
林老师是早些年镇上拨下来的支教老师,说是老师,只不过也是个空有高中学历的镇上村民罢了。
在村里教书的时候,碰到了他现在的媳妇,两个人相看对眼,结婚定居,这两年还生了个好看的儿子。
他是村上学校唯一一个老师。
这下,林老师一死,学校也开不成了。
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奶奶正提着小水壶,浇院里逐渐长大的西红柿苗。
心下一紧,手松壶落,磕掉的盖子不断往出溢水,田里的苗也被淹了个透。
她顾不上招呼我,急忙往林老师家跑。
我扶着门框,小小的身子踩在门槛上。
看着院里不断被浸泡而死掉的苗。
惋惜地叹了口气。
林老师一家的死相,比旺叔和贵哥的更可怕。
年幼的孩子、妻子、林老师,一家三口的尸体整整齐齐的横在院中。
而他们的头,却齐齐被割下,放在猪圈旁的草垛上。
好事儿冲进院子里的女人全被吓了出去。
原因无他,只是那三个血淋淋的头颅立在那儿,实在可怖。
胆大些的男人也不敢靠近,只是在院里讨论着,他们到底得罪了谁。
直到奶奶的到来。
大家像找到救命稻草似的,一窝蜂地涌上来。
「喻老太,你看看这…」
「喻奶奶,林老师他们…」
奶奶挥手打断了他们,平时和蔼的脸上一脸严肃。
那三具尸体齐齐整整地躺在大院里,死的时间不久,还能看到血从断头处往外渗。
断骨处的森森白骨看得格外明显,依稀能分出是颈骨。
除了没头,其他都与正常人无二。
反观那三颗头,居高临下的看着众人,个个眼睛瞪大,死不瞑目。
嘴被撕扯成诡异的弧度,好像在看着大家笑。
站在院里的众人不寒而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