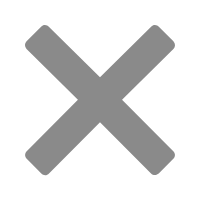-
回魂夜惊魂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第 1 章节
1
我将车速提到最快,飞速往村里赶着。
脑子里只有一句话:「儿,你爷爷快不行了,他想见你最后一眼…」
怎么可能?
爷爷身体一直不错,而且上次回去时,他还答应下次等我回来,带我去看村里的庙会……
车开得快,有几次都差点撞上前车。
我泄愤似地狠捶方向盘,忍不住趴在上面呜咽起来。
再抬起来头,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前面。
右脚快踩进油箱里,飞驰着往村里赶去。
村口的人只看到一阵尾气,一道深深的车辙印,一辆车已经飞过了村口,朝里开去。
村口没修路,空气里都是泥土飞扬,我直直把车开进去,停到家门口。
“砰”的一声,我关上车门。
门口出来一个男人,佝偻着背,背上仿佛背着一个大疙瘩。
这是我爸,他生下来就是罗锅子——跟电视里那个宰相似的。
我急忙问道:「爷爷怎么样?」
爸爸摇摇头,不说话。
我三两步跑进屋,看着躺在床上的那个老年人。
可能确实将至大限,他露在外面的双腿已经覆了些紫斑,和老年斑混在一起,乍一看确实看不太出来。
深陷的双颊上凹出了坑,两颗微凸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,半张着嘴好像要说什么似的。
本来微胖的爷爷如今变成了这副样子,我抹抹眼角,跪着行至床边。
「爷,是我,我是灵一啊!」
这名字是爷爷取的,他说,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
爷爷眼角突然流下一滴泪,颤抖着伸出手想抓我。
我赶紧将手递上去。
跟在身后进来的爸爸看到这一幕,刚抬起、准备进来的脚又放下,退了出去。
他一走,爷爷跟刚才躺在床上的样子比又好了一点。
好在能开口了,他颤抖着声音:「孩…孩子,你回来了……」
我点点头,努力凑前去。
爷爷伸出右手,动作缓慢地掐了几下,颤巍巍地往胸口盖了下去,一股黑气涌入他心口。
我惊讶于爷爷的举动,忍不住道:「爷爷,您这是……」
爷爷慢慢抬眼看我,眼里含着一丝震惊:「你能看到?」
我心里有些嘀咕,但还是忍不住点点头。
爷爷叹了口气,又鼓着胸膛笑了起来,这声音一点也不像个临终的人。
「这都是命,这都是命啊……」
我紧了紧抓着爷爷的手,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爷爷看着我的眼睛,慢慢道:「我快死了,无药可医。接下来的东西,你听好了。」
他别过头去,看着窗外,给我讲了个故事。
2
1952年,这里遇上了难得的大旱。
以庄稼为生的村里人自然要饿肚子了。
一天,村里来了个男人,他从小跟师父学茅山术,靠着替人害人,勉强混口饭吃。
他术法奇怪,与正派不同,是黑茅山,属阴邪之术。
来这里,也只是为了接单做生意。
男人返程走的时候,遇到了个年轻女孩,两人一见钟情,瞒着所有人在一起了。
年轻女孩也没有父母,住在废弃的窑洞里。
每天饥一顿饿一顿,一个多月了没吃过口粮食,饿得狠了就去刨土、挖野菜、甚至啃树皮。
男人心疼她,跟她一起在村里定居了下来。
没过多久,两人就生了个孩子。
不知是男人坏事做多了还是女人怀孕时营养不足,孩子生下来竟然就是个驼背。
背上隆起一大块骨头,看着十分怪异。
女人不想要,可男人觉得,这毕竟是自己的孩子。
就这样,孩子窝在家里,一直长到了二十来岁。
二十岁那年,女人得病死了。
得的是怪病,听说死的时候身上布满了荆棘皮。
怕引来怀疑,也怕黑茅山术败露,男人瞒着村里人,将女人的尸体烧了。
在当时,火葬可是村里人避讳的,被认为是对死人的大不敬。
从那以后,男人就带着孩子,悄无声息地在村里生活。
男人认为是术法不祥才会让女人得病身死,此后,就再也没用过茅山术了。
当然,也就失去了能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。
眼看孩子活到二十多,准备娶妻生子了。
可家里既没钱,孩子又长得这幅样子,正常人家的姑娘谁能来?
男人犯了愁。
不行,家里单传,不能断了香火。
一筹莫展的时候,村里突然传来消息,不知从哪闯进来个疯女人,甚至咬掉了路过村民的耳朵。
村长说,让各家各户紧闭大门,等疯女人走了再去农作。
男人眼睛一亮。
女人?
在家家户户闭门不出的时候,男人拿着炮仗点着了扔出去,把疯女人骗过来了。
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,疯女人竟在他家留下了,还嫁给了他的罗锅儿子。
男人满意地笑了,虽然女人智力不好,但能生孩子,就是好的。
结婚没多久,疯女人怀孕了。
临产那天,他请了产婆。
待了好长时间,产婆哆嗦着双手,闯了出来,抖着声音告诉他,疯女人的孩子生出来就没了气息,钱都没要,就跑走了。
男人着了急,顾不上纲常伦理,闯进去一看,疯女人支着双腿,孩子刚从下身掉落出来。
血流了一床不说,这孩子脖子上结结实实地绕着脐带,活活勒死了。
男人一急,眼看疯女人气息奄奄,他动了念头。
用黑茅山术,将疯女人余下的七十年寿命,全借了过来,传给了那个本该死去的孩子。
孩子脸色慢慢变好,冰冷的体温也渐渐回暖。
只是疯女人,就这么死在了临时搭的产房。
男人冷眼看着这一切,出门后,只告诉儿子,他有自己的孩子了,女人难产死了。
事后,简单把女人用草席卷了,半夜扔进后山坟圈子。
3
我边听边愣怔着。
罗锅儿子、疯女人…
难道这是爷爷的故事?
那个本该死去的孩子,是我?
怪不得,我从小就没见过妈妈,爷爷说,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。
原来背后,竟藏着这种事。
我正发呆,爷爷猛地吐出一口血。
「爷爷!」
我忍不住伸手去堵。
可血却像泉水一样越来越多,糊了我一手。
爷爷脸上挂着血,却看着我笑:「娃…以后就靠你了…」
靠我什么?
我还没问出口,爷爷手一垂,挂着笑就闭上了眼睛。
我趴在爷爷尸体上嚎啕大哭。
这是看我长大的人啊……
爸爸听到我的哭声,冲进来将我一把拖开,指挥些叔伯村民们进来抬走爷爷的尸体,放进黑木棺材。
我揉着眼睛:「爸,你这是……」
爸爸撩起帘子,看了我一眼:「你爷说了,他一走就立刻入棺,不用过了头七,五天后立刻下葬。」
我看着僵硬的尸体被装入冰冷的棺材。
不敢相信刚才我还揽着听故事的人,现在已经跟我走到了两个空间。
“砰砰砰”……
突然传来一阵敲击声,我被吓了一跳,循声看去。
爸爸驮着背,脸贴在窗户上,重重地压出了痕迹,叫我过去。
「等爷爷下葬了,你就走吧。」
我点点头。
4
一夜无眠,我躺在爷爷生前的地方,满脑子都是临终前听到的那个故事。
会黑道术的男人是爷爷,罗锅儿子是爸爸,脐带绕颈借寿而活的人是我。
呵我们这一家子三个男人,没一个好东西。
可是,我那个素未谋面、甚至被骗来生孩子、被借寿而死的妈妈呢?
她长什么样子?她如果还活着,会恨我吗?
还有爷爷的事,黑茅山是什么?我竟一无所知。
睁眼到天亮,爸爸进来给爷爷收拾遗物。
我看着他匆忙的背影,问道:「爸,黑茅山是什么?」
他动作一顿,狐疑地看着我:「什么黑茅山?」
眼里是疑惑,我看不错,难不成爷爷没告诉过爸爸?
我摇摇头,打着哈哈道:「没…我做梦了…」
爸爸嘀咕着:「你这孩子,从小一做梦,第二天就爱胡言乱语……」
我又接着问:「那,妈妈呢?」
爸爸边翻箱倒柜的找着什么,边回答。
「不是说过了吗?你妈妈难产大出血死了,一直问……现在不如多想想你爷,他那么疼你……」
我翻了个身,爸爸从小就爱唠叨我,我们关系并不好。
如果这次不是爷爷出事,我怕是好久都不会回来。
一夜没睡,只是这躺下的片刻,迷迷糊糊,我竟睡着了。
只见梦里,爷爷坐在这张床的床边,嘴角淌着血,只重复跟我说一句话。
「未来灾,明哲自保即可」
未来灾……是未来会碰到的灾,还是说这灾不会来?
我陷入了沉思。
「别睡了,快出来!」
爸爸掀开门帘,带着愠怒地看着我。
我着急穿上鞋,一低头,却看到床单边角处滴着一滴血。
那不是梦!
爸爸弯着腰带着我出去,给屋里一干人赔着笑。
「娃昨天太累了…」
村里人一副了然的样子,虽然他们不喜欢我爷爷,但看样子对我爸还不错。
只是,这屋里竟然全是男人!
「没事,大侄儿睡会吧,过几天才入土呢……」
我转着头,屋里家具早就被搬到了院儿里,这里现在已经布置成了停棺的灵堂。
黑白色布景,中间挂着个大大的奠字,来的村民都是一身黑衣。
除了爸爸,他早就换上了麻布衣服,腰间挎着根粗绳子。
这在我们老家,叫披麻戴孝。
爷爷的照片就摆在灵堂中央,照片里的他竟然是个年轻人的样子。
怒目横视,还有点凶神恶煞。
我只多看了两眼,便觉得浑身不太舒服。
椅子上坐着个男人,一边抽着旱烟,一边也在看那张照片。
「哥,你咋选了个这样子的,灵老爷子看起来可有点凶啊哈哈。」
爸爸正在给别人倒茶:「辛苦…辛苦…那个啊,是唯一能在家里找到的照片了,那会连饭都吃不起了,哪有钱去拍照片。」
男人掐了烟,不置可否地笑笑。
我揉揉发疼的头,目光下移,看向灵堂中心的黑木棺材。
是我眼花了吗?
怎么有个黑色的东西爬爬蹿蹿的。
我向前走了两步,大家以为我要给爷爷上香,也就没管。
本来蠕动的东西此刻却停止了。
我越凑越近,那是……
5
黑东西竖着瞳直袭我面门,我这才看清楚,这分明是条通体乌黑的蛇!
我躲闪不及,被它一口咬在脖子上。
捂着两个血洞,我大叫起来:「啊!」
事情发生得突然,一屋子人竟然没有一个发现的。
直到听到我的声音,他们才一个个围上来。
在看清后到底是啥后,又赶紧离我远远的。
我忍不住冷哼一声,呵,这就是人性。
黑蛇倏地一下就不见了,不知是爬进了棺底还是棺里。
只有脖子上的两个洞告诉我事情确实发生了。
我看向爸爸,试图用目光求救,可他也躲在人群后,不敢碰我。
「我听有人说,黑蛇爬棺,必有妖惑……」
「不应该啊,他爹生前是道士,怎么会……」
「万一是妖道呢……」
「是啊,我听说,他娘就是被他爹害死的……」
……
村民们一个唾沫一个钉,好像要把我和爸爸砸进墙里似的。
最后还是有个胆子大点的男人,上来看了看我。
「孩子是无辜的,别再被蛇咬死了……」
男人靠近我,贴在脖子上看了许久,又伸出手摸上那个血洞。
「别!」
我还来不及制止,他就两指搓开看了看,然后说。
「没事,不是毒蛇。」
我松了口气,两眼一黑,晕了过去。
「儿子!」
“哄”的一声,爆发了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。
我只觉得身体一轻,好像在空中飞着,又好像被人背起来了。
不是毒蛇,也会死吗?
头一歪,这下,彻底昏迷了。
6
一只干枯的手抓住我,我猛然睁开眼睛。
看着这个残肢,忍不住喊出了声:「谁!」
人影本来在黑暗里隐着,被我一叫,只露出一只眼睛。
那只眼睛,是爷爷的!
「快跑,那个疯女人见我已死,就要回来了!」
我胳膊被死死握着,想抽也抽不出来。
对着人影喊道:「什么疯女人?」
爷爷从黑夜走出,穿着一身白色道袍,道袍底下有线绣的黑色“茅”字。
看他这身打扮,还真像个术士。
爷爷摇摇头:「你现在赶紧跑。等这疯女人回来就晚了!不光要你们的命,还要屠村!」
我一头雾水,如果是故事里的疯女人的话,她应该早就死了,怎么可能回来?
突然,地面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,我看过去。
是那条咬我的小蛇!
蛇身绕着爷爷的腿缓缓向上爬,蛇尾绕着爷爷肩膀处,立着身子,竖着小脑袋,双眼像铜铃似的,盘在后面看着我,不断冲我吐着蛇信子。
而爷爷就像他的饲主似的,时不时摸摸它的头。
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幕。
突然,小蛇猛地伸直身子,像白天那样,再度向我飞来。
我一惊,往后退了几步,地上却不知什么时候长起了荆棘。
一丛丛从脚下窜出来,将露在外面的皮肤划得全是红痕。
眼见逃不过这条蛇,我抬起双臂挡住脸,紧闭双眼。
一阵白光晃过,再睁开,是爸爸焦急的目光。
难道,又是梦?
胳膊上传来一阵刺痛,我低头一看,那里赫然有几个红色的指痕。
不,不是梦!
爷爷说的是真的?
「儿,怎么样了?你还好吗?」
我点点头,看着爸爸,伤口处已经被抹了药,冰冰凉凉的。
爸爸松了口气,正准备走,我拽住他的袖子,一字一顿说:「爷爷说,疯女人来了,让我快跑…」
爸爸一听变了脸色,忙上来捂住我的嘴。
「说什么胡话?哪有疯女人?外面人多,你少说话……」
说罢,就像沾染了什么晦气东西似的,在衣服上不断擦着手。
我不懂,为什么每次听到疯女人这几个字,爸爸也跟失了神智似的。
而且看样子,他好像确实不知道疯女人的存在,不会是爷爷封了他的记忆吧?
我继续道:「可爷爷说,让我赶紧走!」
爸爸弯着背,侧着脸剜了我一眼:「不许走!等你爷爷下葬了才行!」
「爸!」我坐在床上一喊,他走得更快了。
我猛地敲了下床板,颓然地靠在床头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