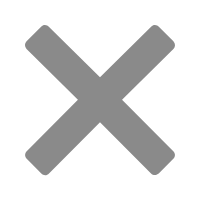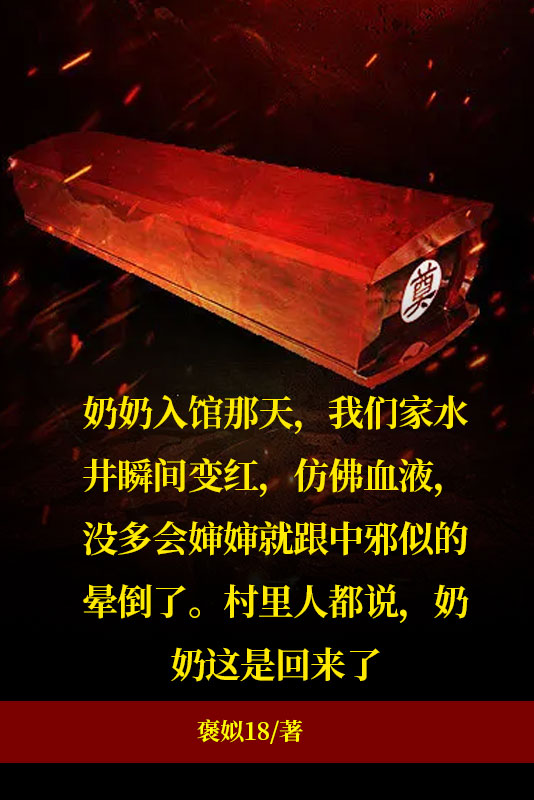
-
夺寿之仇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第 1 章节
1
「儿子,赶紧回来一趟吧,你奶奶……去世了。」
电话那头,是爸爸略带疲惫和焦急的声音。
「好……」
听着电话挂断的嘟嘟声,我有些呆滞地看着手机。
我爷爷走得早,前些年,奶奶又突然患病,瘫痪卧床,爸爸兄弟三人轮流伺候奶奶,这断断续续也得有五六年了。
虽然我们随时做好了奶奶不堪病痛折磨而去世的准备,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,还是觉得很突然。
来不及多想,我装好手机和随身证件,赶紧跟导员说了一声,坐上最近的一班火车就往家赶。
无论如何,我都要在奶奶入土为安前,再见奶奶一面。
我坐在车厢里,回想着小时候奶奶对我的好。
以及——奶奶的病。
高二那年,一向身体硬朗的奶奶突然得了怪病。
先是头疼,再是四肢疼,最后竟然全身疼得下不了地。
爸爸和叔叔为了奶奶的病,那几年跑了大大小小十来家医院,得到的结果都是病情复杂,小城镇机器不好,检测不出啥,再回去观察观察,犯病的时候再过来,不想等着观察的话就去大城市看。
哪有人犯病了才来治病的?
奶奶怕花钱,不肯跟我们去大医院看病。
气得叔叔直骂小城镇的医院,都是庸医。
奇怪的是,接二连三的去过医院后,奶奶身体多少康复了一点,竟然能下地走动了。
但好景不长,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。
要强的奶奶在身体好了一点之后就拿着水桶去地里了,这一走,一整天都没回来。
晚上,叔叔不在,我和爸爸作为家里的男人主动去找奶奶,打着手电一路沿着自家田地去找人。
我们是在二里地外,自家地里发现奶奶的,奶奶躺在地上,水桶里的水完完全全地洒了一身,一点没往地上滴。
被发现的时候,奶奶口吐白沫,全身还在不断抽搐着,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。
大半夜的,我赶紧去找了乡村医生来,可是没办法,奶奶被抬回来后就瘫痪在床了。这下,彻底不能动弹了。
没有人知道奶奶得的是什么病,但村里人都传,奶奶中邪了。
说的人一多,叔叔迷信,直接去隔壁村请了神婆子回来,想看出个一二三来。
神婆子掐指一算,又绕着我家转了好几圈,振振有词的说。
「你家的土地风水不好,你妈又老去干活,时间长了自然会跟上不好的东西。而且,出事那天路上颠簸,没抬稳水桶,水洒出来湿了土地庙,破了龙根,惹恼了土地神,这是对你妈的惩罚。」
叔叔赶紧询问:「那怎么才能给土地神道歉呢?」
神婆子眼睛一转,嘿嘿一笑:「这好办,给我老婆子3万,保准你药到病除,你妈立马下地走路。」
姑姑正好端着奶奶的洗脚水从里屋出来,听到这句话直接向神婆子一泼。
「哪里来的老妖婆,年纪这么大还骗钱,给自己积点阴德吧!」
神婆子往旁边一闪:「小丫头,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既然你们不信,那我只好走咯。等以后有事儿,记得带两只鸡一只鸭来找我啊。」
姑姑冲着神婆子的背影啐了一口: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」
叔叔不敢惹这个妹妹,只能跟在神婆子背后连连道歉,把她送出门去。
2
自从奶奶瘫痪以后,三家就开始轮流照顾老人了。
但俗话说得好,久病床前无孝子,这伺候人的活哪有那么容易?矛盾自然也就升级了。
婶婶是个泼辣、甚至有点不讲理的女人,听我妈说结婚的时候由于奶奶续的被子少了二斤棉花,跟叔叔大闹了一场,差点离婚。
这么多年过年,也基本上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家。
在我印象里,每年为数不多跟她见的几面都是在跟奶奶吵架,她脾气不好,我是不太敢跟她说话的。
这下好了,听到要照顾这么个瘫痪病人,彻底发飙了。
我们都不知道叔叔是怎么说服她的,只是那段时间见叔叔,他总是头发凌乱、脸色欠佳,但最终,他们还是第一家接走奶奶的人。
就这样“相安无事”地过去了五六年,终于,奶奶去世了。
我上大学的时候,总能听得爸爸跟我抱怨,婶婶对奶奶不好,姑姑对奶奶不好。
可又有什么办法呢?人又老又病,本来就是这样任人揉搓的。
我一边象征性地安抚爸爸,一边筹划着准备等毕业后就把奶奶接走,伺候她余下的人生。
可是还没等我毕业找到工作和房子,奶奶就已经离我而去了。
我在车上想着想着,竟然因为劳累睡着了。
我是被列车员推醒的。
「旅客您好,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,请您收拾好行李,尽快下车。」
我揉了揉头发,不慌不忙地起身,去洗手间洗了把脸,带好东西下车了。
在出站口,我看到了来接我的爸爸。
爸爸穿着一身灰扑扑的黑衣服,袖口上别了个写着“孝”字的牌牌,脸色乌乌的,眼圈也黑青黑青的,胡子没刮,再加上乱糟糟的头发,活像个流浪汉。
长大以后,我就跟爸爸没什么话好说了,从后视镜里,我偷偷观察着爸爸的样貌,老了不少,也疲惫了不少。
只是这脸色,怎么能差得这么离谱呢?
等红绿灯的时候,爸爸主动发话了:「儿子,你奶奶去世了,咱家…也发生了点怪事,咱们送完你奶奶,就回家。」
怪事?这难道就是爸爸面色不好的原因?难道当年村里人和神婆子说的是真的,奶奶真的中邪了?
我没敢说什么,点点头,眼看离奶奶家越来越近,我心脏莫名“咚咚咚”地起伏,跳得厉害。
3
爸爸停好车,我从车上下来,一抬头,一副黑木棺材直直放在街边。
「这是……?为什么不放到院子里啊?」
哦对,奶奶家是有个专门种花种菜的小院的,现在由于没人居住也荒废了,我看大小差不多,刚好能放下。
爸爸面色不佳,没理会我,只是带着我穿过小院,往屋里走。
我回来的时候是下午,本应该有来吊唁的邻居和敲锣打鼓的白事喇叭,此刻却都没有。
姑姑不在,叔叔坐在沙发上抽烟,而婶婶,则在客厅的床上沉沉睡去。
我进屋,叔叔摁灭烟头:「娃娃回来了。」
我点点头打了个招呼,看向婶婶:「婶婶累得睡着了?」
叔叔叹了口气:「唉,你爸都跟你说了吧?你婶婶已经睡了三天了,这几天她跟中邪似的,总是白天睡觉,晚上满院子跑,给我们都吓得不轻。至于你姑姑,胆小怕事儿,说她身体不舒服,得回家一趟拿点药,这一走,也走了三天。」
怎么会?
我把行李放下,突然口渴想喝水,于是自己走到院里的水井旁提水喝。
爸爸叫住了我,递给我一瓶矿泉水:「喝这个吧,水井……」
直觉告诉我,水井有问题,我不信邪,偏要去看个究竟。
如果真跟我想的一样,是奶奶的话,那她也一定不会伤害她最喜欢的大孙子。
我不顾爸爸的阻拦,走到水井边,踢开上面封着的铁制盖子。
向下看去,水井里黑乎乎的,什么都看不到。
哪有那么玄乎?这不是正常的?
我转动旁边的摇杆,嘎吱嘎吱的,好像年久失修了似的,准备把桶放下去接水。
听到“咣当”一声,看来是水桶沉底了,等了三五秒,我就开始往上摇。
奇怪,几年不用,这个杆子沉得令人发指,我居然差点就转不动了。
这感觉就好像,有人在下边拽着一样。
想到这里,我伸出头向井下看去。
水桶里,一双莹绿色的眼睛正忽明忽灭,紧盯着我。
「啊!」
除了电视里,我哪见过这东西?赶紧松手把水桶扔进井里,连滚带爬地往后跑。
身后又突然撞上一个软绵绵的人。
「妈呀!!!」
我吓得闭上眼睛,身子有些发抖。
「别怕,是我。」
爸爸安抚地拍着我,他说,前几天姑姑也是这么被吓着的,然后就走了。
没人知道井里的东西是什么,也没人敢下水去看看。
爸爸替我把桶摇上来,但除了眼睛,让人更恐惧的是水桶里的竟然不是水,不对,甚至可以说,井里的不是水——
看起来像是被稀释的血液。
神婆子?神婆子呢?
我问叔叔,为什么不把她请过来。
叔叔告诉我,怪事一发生,他就提着神婆子要的东西去寻她了,来到隔壁村却被告知神婆子有业务出了远门,得一周才能回来。
算算这一周的时间,正好就到了奶奶的头七。
而我们这里的规矩,人只有过了头七才能被下葬,更有人家舍不得死者的,足足停尸半个月才会去下葬,这期间是留给人们随时来送别吊唁的。
奶奶入馆那天就发生了井中血液的怪事,再加上没多会婶婶就跟中邪似的晕倒了。
村里人都说,奶奶回来报仇了,吓得谁都不敢来吊唁,怕死在我家。
报仇?
我看向爸爸,爸爸却摇了摇头,等叔叔离开了才跟我说。
原来,奶奶是死在叔叔家的,这么多年,婶婶从来没有好好对待过她。
爸爸回去看最后一眼的时候,奶奶身上起着大大小小的褥疮,有的都烂得看到了骨头。
奶奶临终前,恨恨盯着婶婶卧室的位置,死不瞑目。
我捏紧了拳头,突然想就这么算了,不帮她了,她罪有应得。
4
入夜了,爸爸让我开着灯别睡着,据说,这几天晚上发生的事,比白天更恐怖。
我听话地开着电视拉着灯,爸爸和叔叔都不在,有个声响还显得没那么害怕。
越是安静,越是爱胡乱猜测。
婶婶还是昏迷着,叔叔不堪折磨也出去散心了,家里只剩下在外面不知道忙什么的爸爸和屋内听电视的我。
“滋……”
是奶奶的老式收音机声,天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拔了出来,收音机好像在接收着什么信号一样滋滋啦啦的发出声音。
我关了电视,想更真切地听听到底是哪发出来的。
怎么回事?我拿起收音机,使劲拍了拍,嗡嗡的声音没有了,把它贴在耳边,里面的声音渐渐清楚。
「我想你...」
啊!是奶奶的声音。怎么可能?
慌乱下,我准备把天线按回去,可能收不到信号就传不出来声音,天线却跟钢筋似的,怎么都按不下去。
我打开后盖,原本应该装有电池的位置此刻却空无一物。
这个收音机甚至没安电池!
那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呢?
爸爸推门进来,看到我手机拿着收音机,脸色一变。
「这东西怎么还没给你奶奶放过去,真是的。」
说完,拿着这玩意儿快步走了出去,听说人生前喜欢的东西,死后必须得陪葬。
我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,跌坐在沙发上,心突突地跳着。
正当我刚刚平复的时候,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,我循声望去,竟然是我那昏迷了一天的婶婶。
婶婶“腾”地一声从床上坐起来,双腿伸直,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
披头散发,脸色铁青。
这屋子里可是就我俩,看她这个神志不清的样子,我有些害怕,一步步倒退着,试图往院里躲去。
婶婶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原来坐着的位置那,突然哈哈地大笑起来。
笑声本来是不可怕的,可她一直不停,那声音渐起,音量从小到大,回荡在整个屋子里。
笑到最后还有些抽泣声夹杂着。
我推开门往院里跑,婶婶也跟着我到了院里。
她的目光定格在外面,好像穿过小院看到了外面的黑木棺材,眼里满是留恋。
正当我壮着胆子准备问问的时候,婶婶身体突然一阵抽搐,每个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,脚步也像跳机械舞一样,在原地扭动起来。
「爸!」毕竟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,我焦急地喊道。
爸爸从外面慌乱跑进来,看到婶婶这一幕,叹了口气:「又来了。」
还没等我张嘴,婶婶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,双手揉着自己本来就乱七八糟的头发,脸上涕泪横流,嘴里念叨着什么“妈我错了”。
接着她抬起头,目光炯炯地看着那口水井。
然后——疯了似地开始绕着水井奔跑,有几次还身子一歪,差点掉到井里去。
婶婶一边转着圈跑,一边双手向后挥舞着,好像在驱赶什么。
我被这一幕惊呆了,作为唯物主义者,我是不太相信鬼怪的。
可是现在也不得不信。
爸爸说,婶婶这几天很少有清醒的时候,一旦清醒就会说,奶奶让她偿命,在院子里拿着拐杖追着她打。
一开始,大家都觉得婶婶是做贼心虚,胡言乱语,也就没人放在心上。
直到持续时间长了,大家才开始怀疑。
不,这分明就是真的!
刚才,我明明看到,月光下真的有个白影子闪闪烁烁,跟随着婶婶,不,也有可能是引领着婶婶。
甚至,那白影子路过我的时候还稍微停留了下。
5
待在这里的第三天,也就是奶奶去世的第六天。
本来身体健康的我这几天突然觉得身上特别沉重,提不起来劲,能不说话就不想说。爸爸看我的样子,怕我也受什么影响,决定等奶奶头七结束下葬了,我就赶紧离开这里就回学校。
这两天,婶婶白天昏迷,晚上就满院子乱窜,一会跑到井边,一会跑到小院里拔野草,我们一致认为,确实是奶奶回来了。
叔叔一天天往邻村跑着,我们一天天掰着指头等头七。
下午,昏迷的婶婶脖子上突然起了连片的疙瘩,那疙瘩足足有拇指水煎包那么大,一个摞一个。
疙瘩看起来非常恐怖,有的上面有粉刺那样的白色点点,一碰好像还能流出脓来。
我们都不敢靠近婶婶,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传染性。
但是就这样放任不管也不行,这疙瘩让人看着又害怕又恶心的,叔叔让我抽个空,去卫生所买点治痘痘的药,什么皮炎平啊之类的,并且一再叮嘱我,马上就天黑了,要快去快回。
我点点头,在这屋里时间长了有点憋得慌,出去散散心也不错。
我前脚踏出门,后脚就觉得身子轻快了不少,本来懒得动弹的我甚至还能小跑几步。抬头看着这明媚的艳阳天,我却觉得身上阵阵刺骨的寒意,不由得打了个冷颤。
从我家到卫生所,走最近的路得穿过一片小树林。
按理来说,尽管这林子高耸入云,密闭得很,但从小就住在这里的我应该一点也不害怕,但这些天经历的事情,让我忍不住想东想西。
眼看快黄昏了,为了节省时间,我咬了咬牙一头扎进这个看起来有些阴森的树林子。
林子里的树长得个个参天高,都快把太阳遮着了。
越往深处走,越觉得阵阵凉风袭来。
突然看到有个人穿着白衣服站在一棵树后看我,我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走不动了,硬着头皮喊了句谁啊。
没人回答,吓得我赶紧撒丫子跑出了树林。
不对,大白天怎么可能闹鬼?应该是路人吧,一定是我想多了。
我一边安抚自己,一边快步跑到了卫生所门口。
卫生所的护士隔着玻璃观察我,估计一见我这披麻戴孝的打扮,就知道我是哪户人家的孩子,也没怎么问,直接给我拿了几个抹着的药膏,钱也没收,就赶紧催促我离开这里,生怕得了瘟疫似的。
我拍了拍我的孝衣,抚平了衣角的褶皱,撇了撇嘴,这次没抄近道,准备走那个平时有很多老头老太太聊天的大道,远是远了点,图个安心。
本来应该有老年侦查队在这儿聊天的地方此刻却空无一人,阳光洒在身上甚至也没那么暖了。
走了几步,身后传来细细的脚步声,隐隐地感到有人在后面跟着我,奇怪,这里不是没有人吗?
听说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不要轻易回头,否则回头带来的风会把身上的人气儿和火熄灭。
我咬咬牙,不敢细想,加快脚步,一溜小跑赶紧回了家。
回家后看到婶婶脖子上的疙瘩好像又红了点,赶紧把药都递给叔叔,叔叔坐在她旁边给她抹药。
我把那条大道上没人的事儿告诉了爸爸,爸爸说,自从我家闹鬼后,村民们都说最近出门不吉利,基本上家家户户这几天都不出门了,就跟那会口罩时期似的,一个个躲得倍儿远。
至于那个小树林,更不可能有人在了。
我暗暗想道,如果跟爸爸说的一样,真没人在的话,那我看到的白色影子是……
我正想着,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凑了几步准备去看看婶婶,爸爸却在身后迟疑地叫我:「你……」
我回头,不解地说:「怎么了?」
爸爸让我脱下外面的孝衣,我提溜着左右看了看。
这也没啥吧?
爸爸随手一指,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,我惊讶地发现,居然有两个血指印,印在白色的寿衣上!
刚才果然有东西跟着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