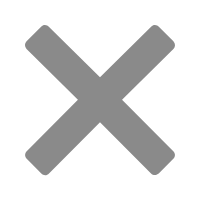-
坏人还需恶人磨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第 1 章节
1
这是我第三次被锁进厕所。
我身上的校服被泼了污水,湿漉漉的黏在身上,散发着阵阵恶臭。
现在已经十一月份了,室内的暖气烧的像火炉,可我现在这幅样子要去了外面,一定会变成一座冰雕。
门外传来她们愉悦而猖狂的笑声,她们一边笑一边用脚踹门。
沈悦大声说:“温文!你不是硬气得很吗?你不是反抗吗?不是告老师吗?”
沈悦是我们学校的扛把子,仗着认识几个校外不入流的混混,就在学校里横行霸道。
她是名副其实的小太妹。
一个月前,那个被她们一直欺负的女生得了抑郁症被迫转学后,她们就盯上了我。
因为我和那个被欺负的女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。
看起来都很不起眼,逆来顺受的那种。
但是我和那个女生不同。
她或许是真的,但我是装的。
我挽起袖子,脚踩上厕所的隔板,胳膊使力,三两下就爬了上去。
沈悦嘴巴里叼着棒棒糖,忙着和身旁的两个女生调笑。
在厕所吃棒棒糖,真亏她能下得去嘴。
她们还没注意到我已经站在隔板上了。
她说:“温文啊,看起来又臭又土,这年头谁还留厚刘海啊,戴个眼镜恶心死了,她这种货色,要饭的都不愿意上...”
她后面那个字还没说出口,我从隔板上一跃而下,稳稳的站在了她面前。
她一脸难以置信,惊慌失措地后退了半步。
她低声咒骂:“她怎么出来的...属猴子的吗?”
我一把攥住了她的衣领。
她不愿意失了面子,强撑着摆出架子。
她抽搐着嘴角哼哼:“怎么样?想打我?你比谁都清楚我爸是谁。”
她挑衅的笑,涂了唇膏的嘴唇勾出讥讽的弧度,她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她家很有钱,她爸常年做海外生意,早些年给学校捐了好几栋楼。
主教学楼的名字就是用她爸的名字取的。
这也是学校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。
上次我冲进校领导办公室,把视频录音乱七八糟的证据摆在领导眼前时。
校领导只对沈悦不痛不痒的说了几句。
校领导的原话是,同学之间小打小闹很正常,只要没闹出人命来,都不是什么事。
而我也是那次才彻底清楚了她家的背景。
沈悦挥开我的手说:“我告诉你,我爸分分钟能让你家那个小破水产公司倒闭,你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。”
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
我说:“求求你了,快让我家倒闭吧,我爸妈到时候要是还能吃上一口饭,就别怪我瞧不起你。”
她满脸震惊:“你这个疯子,你不相信我吗...”
我说:“信啊,我当然信了。”
我抬手就往她脸上扇了个大嘴巴子。
她嘴里的棒棒糖直接被我这一巴掌扇飞,飞进了蹲坑里,但没滑下去。
她们还在愣神,我顺手抄起了一边的拖把,沾着水脏兮兮的拖把头直冲冲朝她脸上去。
她扯着嗓子大声尖叫,脚上连连后退想躲。
她们挑的时间很好,这会正是上课的时候,谁都不会来。
我用拖把给她好好地洗洗脸。
我直接把拖把头糊在了她脸上,脏水均匀地糊满了她的脸。
她没忍住,放声大哭。
她哭着说:“温文!你完了!我要让我爸弄死你...”
我连连点头应答。
我径直去蹲坑里捏起那个棒棒糖,然后塞进了她嘴里。
我抱着胳膊笑着说:“对不起啊,还给你糖,别哭了。”
2
事情闹去了老师办公室。
沈悦坐在沙发上哭得泣不成声,她周围围了一圈老师,都忙着安慰她,又是给她倒热水,又是给她拿来了干净校服。
我就站在她身边,我身上湿透,连头发都在往下滴着水。
那几个老师止不住的向我投来可怜的目光,却没人敢过来帮我。
老师们也一样,忌惮着沈悦他爸,毕竟他爸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他们拼尽全力才得到的工作毁于一旦。
丁老师急匆匆的从走廊赶来,她推门而入,一眼就看见了我。
她蹲在我面前,然后紧紧地抱住了我。
她的怀抱温暖而有力,我可以闻到她发间淡淡的洗发水香气。
我有些愣神。
丁老师今天似乎哪里不太一样了。
她好半天才松开我,她盯着我的脸,眼睛一眨,眼眶里就蓄满了泪水,大颗大颗从她脸上滑落。
我已经做好了被她批评的准备,也想好了说辞和解释。
没想到她开口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:
“文文...太好了!你还活着!真好,我又见到你了,原来我真的...”
她垂下头,声音压的极低,嘴巴小幅度的开开合合。
重生了。
她说的是,她真的重生了。
我不明所以。
虽然不太礼貌,但是我觉得丁老师似乎疯了。
校领导得了消息,把我和沈悦喊去了校领导办公室,身为班主任的丁老师也在场。
一进门,丁老师立刻对着校领导大声说:“我知道沈悦一直霸凌温文,这次沈悦拿脏水泼温文,又拿拖把糊在温文脸上。”
她叉着腰又说:“你要是这次再不管,我不怕把事情闹去教育局!”
丁老师把厕所发生的事完完整整,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通。
我皱紧了眉毛,丁老师叫错了名字吗?
应该是温文把拖把糊在沈悦脸上吧。
丁老师又不在厕所,她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?
校领导揉着眉心:“丁老师,你搞错了吧,这次是温文霸凌沈悦。”
丁老师愣神:“什么啊?不是沈悦在厕所欺负温文,温文这次来办公室告状吗?”
沈悦嘴巴一撇嚎啕大哭:“这次是她欺负我!她用拖把给我洗脸,又把掉到厕所里的棒棒糖塞进我嘴里!”
丁老师扭头看我,用眼神向我询问。
我大大方方的摊开手,点了点头。
丁老师一向镇定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。
最后丁老师和校领导据理力争,不过这次是换丁老师来说那句台词。
这都是同学之间的小打小闹,孩子们不懂事不知道分寸很正常。
校领导一噎,还是想把我通报批评。
丁老师一听立刻开启了狂暴模式。
一向端庄温和的她,叉着腰在办公室和校领导对骂了整整一个小时。
我披着丁老师的外套站在走廊,听着里面乱哄哄的声音,我垂头盯着脚尖若有所思。
最后,不知道丁老师用了什么手段,学校并没有对我和她下处分。
但是我很清楚,沈悦咽不下这口气,一定不会就这样放过我,她爸肯定会替她出头。
一想到家里那个公司要破产了,我就激动了三天三夜。
我得罪沈悦的事情私底下传的沸沸扬扬,大家都在我背后小声的议论着我。
可怜的目光快要把我淹没了。
至于我怎么得罪的沈悦,却没人知道。
晚饭时,我在食堂扒着白米饭,喝着学校的免费汤。
我妈一个礼拜只给我五十块钱生活费。
住校五天,正好一天十块钱。
我抬头时,正好看到端着两份餐盘的丁老师在四处张望。
我和她的目光正好在空中交汇。
她脸上扬起笑,直冲冲的向我走来,把手里那份有菜有肉还有两个大鸡腿的饭放在了我面前。
我点头说了声谢谢老师,就没和她客气的吃了起来。
她用手支着脑袋,盯着我的脸看。
她喃喃说:“我家文文出息了呢,没骨气的小哭包这次终于知道反抗了...”
我放下筷子,我看着她的眼睛说:“丁老师,你是重生了吧?”
她在办公室抱我时,我当时觉得她疯了在胡言乱语。
但是她在校领导办公室帮我据理力争说话时,我觉得她可能是真的。
她愣了一下说:“是,文文,是老天爷让我重生回来救你的。”
我问:“我前一世是什么样子的?”
她垂下头:“你死了,在高考出成绩的第二天。”
完了,看来我高考发挥失常了。
2
丁老师一直都对我很好,是我的班主任,对我格外地照顾。
但是在她重生之前,这种照顾也仅限于同情。
她说前一世快高考时,她生了一场能要她命的大病,临死前,只有我在照顾她。
她的脑袋里长了一个小肿块,本来不要紧,但是因为检查不及时,后来才恶化了。
她说话有一搭没一搭,听得我乱七八糟,但我还是抓住了事情的重点。
她会死,我也会死。
这周末她会去医院检查,我本来想陪她一起去,但是她拒绝了我。
周五晚上,我刚回到家,就在手机上收到了丁老师发来的消息。
她做了全套体检,果不其然发现了脑袋里的小肿块,这次发现的很及时,只需要吃药治疗。
第二天是周六,中午叔叔伯伯会来家里吃饭。
妈妈让我早晨六点半就出去买菜。
因为她说这时候的菜又便宜又新鲜。
可是她平常去买菜也就是十点多,我看她十点多买来的菜和我六点半买来的,都一模一样。
其实她心里也清楚。
她只是单纯的见不惯我,变着法的挑我的刺。
我背着大包小包进了门,家里的热气扑在眼镜片上,凝成了白雾。
我把买菜剩下的零钱数好给了她。
她看见我回来,就没什么好脸色,她嘟囔着说:“怎么这么慢!让你买个菜磨磨唧唧的,不知道我着急做饭吗?”
她仔仔细细数了三遍零钱,发现差了一两块钱。
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塑料袋,看着里面的西红柿,不满意的左瞧右瞧。
她问:“西红柿多少钱一斤?”
我说:“一块三。”
她一听就发了火,指着我鼻子吼:“我昨天买还是一块二!你怎么买就一块三!”
她这斤斤计较的样子,我早就习以为常。
我脱下脚下双开了胶,发黄的球鞋,藏在了鞋柜后的角落。
我解释说:“今天涨价了,菜市场我跑了六家,这是最低的了。”
她一点都听不进去,一直在计较这一毛钱的事情。
她说:“一毛钱你就不当钱了是吗?我们辛辛苦苦上班供你吃喝,供你读书,你吃的喝的都是我们的血汗!”
好窒息。
她拍着胸口一副痛彻心扉的样子,嘴巴上不停的数落我。
我垂着头道歉,连连保证下次不会了。
她这才肯放过我。
我回了房间,轻手轻脚合上门。
我的房间是拿杂物间改的,还没家里的厕所大。
一张单人床,一张小桌子,几件衣服和堆在地上摞得像小山一样的书,堆在狭小的房间里。
就是我的全部家当。
我在书桌前坐下,这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我的同班同学,甚至老师,都觉得我家里很穷。
毕竟没有人在北方的寒冬里还穿着秋季校服,里面套着三件卫衣。
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订冬季校服的棉袄。
我说我怕热。
零下十几度,热得我直哆嗦。
我讨厌下雪,虽然下雪时很暖和,但是雪融化的时候是最冷的。
可实际上我家里一点也不穷,甚至是略高于小康水平,算得上富裕。
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,他在私立学校念书,一年学费三万八。
我和他长的同一张脸,可却是截然不同的待遇。
他是天上的骄阳,我就是阴沟里的老鼠。
他一身名牌,随随便便一双球鞋都要几千块。
爸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
纵使他是个不学无术的混球。
我拿出丁老师塞给我的习题,一边翻书一边做了起来。
我想念书,我想考大学。
我想逃离这个地方,越远越好,一辈子都不会被他们找到。
只是,现在还不是时候,我还要忍。
3
中午时,叔叔伯伯们来了,还有年轻漂亮的婶婶。
她乌黑有光泽的头发披散着,脸上涂了眼影,还擦了口红,穿着保暖又时尚的羽绒服。
我跟着妈妈站在门口,脸上赔笑开口挨个叫人。
“叔叔伯伯好,婶婶好...”
妈妈戳着我脑袋厉声说:“让你叫人,你声音这么小谁听得到!你有没有家教?大声点再叫一遍!”
我点头,又大声叫了一遍。
婶婶打着圆场:“叫过啦,我们都听到了,文文就是乖,还是生女孩好,不像男孩,太淘气。”
婶婶嘴上说着生女孩好,可是每次她提起她的儿子时,脸上都是难掩的骄傲神色。
饭桌上,爸爸和叔叔伯伯们忙着喝酒,时而会调侃几句一点都不有趣的荤段子。
他们对着妈妈做的菜挑三拣四,妈妈就笑着说她的错,是她厨艺不精。
弟弟没出来吃饭,因为他每天打游戏到凌晨四五点,每天下午才会起来。
就这样,妈妈还觉得他学习辛苦。
我正要夹菜,一抬头不小心就和叔叔对上了视线,我迅速移开目光。
叔叔眯着眼睛说:“文文也长成大姑娘了啊,现在的小姑娘发育的真好...”
我拢了拢衣领,埋头扒饭,没有说话。
要不是家里来客人,平常我是没机会坐在桌子上吃饭的。
我听见叔叔又说:“文文得多吃点,身材好了长大才不愁嫁,现在流行那前凸后翘...”
他拿着筷子,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,生动形象,惹得大家一阵笑。
我心里恶心得很,放下筷子就说要带花花去散步。
花花是我养的狗。
我给花花套上绳子,它开心的围着我转圈圈。
妈妈白了我一眼嫌弃的说:“整天就知道弄你那个死狗,一个畜生比人的地位都高了,也没见你好好伺候伺候我...”
叔叔满脸通红,他打了个酒嗝说:“这狗白白胖胖的,拿来炖肉最好了,狗肉好吃,大补...”
爸爸点头附和:“是咯,拿来做下酒菜。”
我把花花抱起,揽在怀里,有些生气的说:“你们胡说什么?”
妈妈一把拧上我的胳膊,她瞪起眉毛:“大人开几句玩笑而已,你急什么?没大没小!”
她又说:“一个畜生,就算真的吃了,再养一条不就好了。”
我抱紧了花花,转身穿上外套,跑出了门。
昨天下的雪已经被扫干净,只留花坛里薄薄的一层。
哈出的热气变成白雾,被凌冽的寒风吹散。
前年夏天的一个暴雨天,我在路边捡到了花花。
它小小一团,缩在草丛中害怕得直打哆嗦,用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。
在那一瞬间,我在它身上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
等我回到家时,叔叔伯伯们已经走了。
我照旧洗了碗收拾了桌子,就钻进了我的小房间。
我正在解一道很有难度的数学题,辅助线画了好几条,似乎都没什么思路。
可丁老师说这和高考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是同类型。
突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。
弟弟顶着黑眼圈和乱七八糟的头发闯了进来。
他开门见山的说:“我放你那的东西呢?”
4
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烟递给了他。
他迫不及待接过,他下意识想把门反锁,却发现我房间的门根本没有锁。
其实我的房间本来是有锁的。
之前我把门反锁,在里面换衣服,我妈拧不开门就一直砸门,我在里面说什么她都不听,最后直接把门锁卸了。
她说我都是她生出来的,要什么隐私。
弟弟拿出一根叼在嘴里点上,猛吸了一大口。
上个月,我和他刚过了十八岁生日,他就迫不及待开始学着抽烟。
他说,要有仪式感,而这是成年的仪式之一。
爸妈虽然疼爱他,但是却不允许他抽烟。
上次被爸爸发现后,断了他一个礼拜零花钱。
于是他就让我帮他藏烟。
因为在这个家里,没有人会注意到我。
一包烟三十五块,他给我四十块。
我自私的想让他多抽点,因为五块钱够我多吃五个馒头。
他靠在门背后,一边抽烟一边调侃我。
他说:“你学那么多有用吗?爸妈早就给你安排好了,高中毕业就嫁人,听说那男人是二婚,但是家里有钱。”
我握紧了笔,没有说话。
我见过那个男人,肥头大耳挺着啤酒肚,一见到我,就不怀好意的想摸我的脸。
听说他家里是开矿场的,愿意给我家十多万的彩礼钱。
我家里缺的不是那十几万,缺的是权。
而那个男人认识很多高官。
卖掉一个不重要的女儿,换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利。
再划算不过了。
弟弟突然向我走了过来,眯着眼睛打量我的脸,他吐了一口烟在我脸上,我被呛得直咳嗽。
他说:“温文,其实你长得挺漂亮的,毕竟我长得这么帅,你顶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脸,又能丑到哪去?”
他要摸我的脸,我立刻躲开,从椅子上弹了起来,警惕的看着他。
他又说:“与其便宜了那个老头,不如先让我试试...”
好恶心,听了他的话,我胃里直翻酸水。
我攥紧了拳头,骂了一句滚出去。
他突然炸了毛,用牙咬着烟,上来就要扯我的衣服。
他把我按倒在地上,手已经探进了我衣服的下摆。
我抬腿顶上他某个关键部位,趁着他吃痛,我一把推开他。
他捂着裆在地上打滚,额角沁出汗,他咬着牙一字一句的骂道:“温文!你敢打我?你活腻了是吗?”
他眼里有些难以置信。
毕竟在这个家里,我从没忤逆违背过他们的意思。
烟头被他丢在地上,闪着忽明忽暗的火星。
我冲他比了个中指:“我是你亲姐姐,麻烦你有点伦理道德,不要和畜生一样行吗?”
他被我惹恼,站起来就要抓我头发。
我比他快一步,我用手指直接插向他眼珠子,又瞄准了他的裆猛踹。
在我持续输出时,身后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
我听到了我妈的声音。
“彬彬,你下手轻点,别又像上次一样把她腿弄折了,还得去医院花钱给她看病。”
话音刚落,就听见她的脚步声。
弟弟一看她要走,立刻扯着嗓子叫:“妈!是她打我!”
弟弟一边喊救命一边去开了门。
他扑进我妈怀里嚎啕大哭。
我妈愣怔地看了看弟弟又看了看我。
肉眼可见的,她的脸逐渐变得狰狞,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。
恨不得亲手掐死我这个亲生女儿。
我的爸妈对我的恨意,在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就有了。
因为我的脐带缠在了弟弟的脖子上。
弟弟出生时,比我小了整整一圈。
与我的结实不同,弟弟身体虚弱,三天两头就要病一回。
我爸妈本来就有很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,这样一来,他们对我就更加厌恶。
我一出生就被丢给奶奶,去年奶奶去世,他们才被迫把我接了回来。
他们对外从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,也鲜少有人知道,他们一家三口里还有第四个人。
我爸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,我妈在一旁紧紧的抱着弟弟,安抚着他的宝贝儿子。
我妈哭着喊着叫我爸打死我。
我爸按灭了烟,开口说:“你吃我们的,穿我们的还不知足,今天还敢动手了,不打不行了,棍棒底下才能出孝子...”
他挽起袖子一步步向我走来,他猛地抬腿踢上我的腿弯。
他想逼我跪下,我咬着牙挺直了腰杆。
他轻蔑地笑了一下,刚要再踢我一脚时。
突然,他的手机响了,发出叮叮当当悦耳的铃声。
他有些焦躁不耐烦,从兜里掏出手机接了起来。
听到电话那头断断续续的声音,他突然变得惊慌失措。
他厉声大吼:“你说什么?破产?怎么可能!”
我攥紧了衣角,肩膀控制不住的一耸一耸。
天知道,我把所有伤心的事情想了个遍,才忍住没笑出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