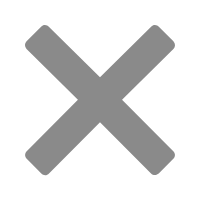-
有糖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第一章
嫁给全京城最俊美的夫君后,我多年不育。
老夫人劝他纳妾,他都冷漠拒绝,待我始终如一。
直到庶妹一袭红衣,在家宴上献舞时,我看到他眼神中藏不住的惊艳。
他言:“阿云,我也是需要传宗接代的。”
他不知道,我的毒已入骨,而那个给我下毒的人,即将成为他的续弦。
1.
我与陆照珩成婚七年,一直不育。
今年初春,我第一次遇喜,可惜没有坐稳,未满四月就不甚滑胎。
炎夏刚至,我的身体也逐渐恢复。后院荷花开遍的那天,陆照珩为我举办了一场家宴。
他牵起我仍泛着冰凉的手。
“夫人,孩子我们总会再有的,即使没有,我也愿意与你一生一世。”
我心头微动,这时,戏台的大幕拉开,丝竹管弦声骤起。
只见,台上的女子一袭红衣,肌肤胜雪,垂珠面帘堪堪遮住半张脸。
她舞步轻移,如一朵盛放的红莲,一出场便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包括我的夫君陆照珩,都在一瞬不瞬盯着台上。
一曲《莲华》舞毕,美人走到众人面前,轻轻摘下了面帘。
原也不是别人,正是来府上看望我的庶妹,沈灿月。
我瞥了一眼身旁看入迷的陆照珩。
“连夫君这样不喜歌舞的人,都看呆了,想来小妹的歌舞,的确动人心怀。”
他是始回过神来,眸色渐暗。
“你姐姐刚失去一个孩子,身体尚未全然恢复,你怎能穿得如此鲜艳,惹她伤心?”
沈灿月有些委屈地跪了下去。
“姐夫,灿月只是觉得姐姐喜欢莲花,想让你和姐姐开心,并没有想那么多。”
她虽身覆红纱,只是略施粉黛,楚楚可怜的样子,倒比我更像病美人。
见我没有说话,家宴上都是侯府和沈家的亲信,纷纷打起了圆场。
“瞧瞧侯爷,对夫人是多么疼爱啊,如此温柔细致,令人羡慕。”
“是啊,二小姐也只是好心,夫人可莫要往心里去。”
陆照珩也满眼歉疚地看着我。
他明明是在向着我,可我心里却微微刺痛。
即使他再隐瞒,刚刚眼中的惊艳与渴望也掩盖不住。
他还不知道,我的毒已深入经脉,至多活不过三个月。
还有三个月,他就可以完成对我至死不渝的诺言。
即使他日后续弦再娶,于我都不算辜负。
只是他,还可以做到吗?
我中毒至今都是个谜团。
如果不是我无意中发现指甲发黑,这毒几乎无声无息,在侵蚀着我的身体。
几日前,我从相识的女医那里诊脉,才得知了这件事,她摇头叹息:
“您小产后身体本就亏虚,又遭人暗害,现在毒已入骨,药石难医。”
2
我是刑部尚书的嫡女,这些年,为了帮陆照珩在朝堂上扫除障碍,很多事都是由我出面,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。
我的夫君是齐安侯嫡子,出身极贵的小侯爷。
可他不是一直都如此矜贵。
他儿时曾不甚被拐走,流落民间多年。
直到十四岁那年才凭借身上的胎记和信物被侯府找回。
我第一次遇见他,就是刚及笄时,女扮男装偷跑出去逛花灯节,遇到了抱着书在破庙里苦读的陆照珩,相谈甚欢。
而我恰巧认出了他身上的信物,帮他恢复了身份。
他重新回去,锦袍加身,为了感谢我的恩情,邀请我去参加侯府的竹林诗会。
那日的诗会上,空无一人。
我永远忘不掉,当我失落回头时,鲜衣怒马的少年郎手鞠一捧夕颜,绚烂的烟火在他身后瞬间绽开。
他俊美的眸子里灿若星辰。
“我第一次见到姑娘,方明白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为何意。”
后来,我们成为了京城里人人艳羡的一对佳偶。
七年了,我膝下没有所出,即使老夫人一再劝他纳妾,他也坚决不肯,一心与我琴瑟和鸣。
他为我亲手栽植的连理枝,今年初夏,其中一棵不甚枯萎,逐渐佝偻枯败。
我沉溺在失子之痛中,无暇顾及其他,而娘家派了妹妹前来陪伴我。
庶妹是闻名京城的美人,年方二八,还待字闺中,求亲的人已踏破了门槛。
姨娘是我父亲心爱之人,沈灿月虽然是庶出,也是在沈府娇生惯养长大,丝毫不比我这个嫡姐待遇差。
她喜欢陆照珩这件事,是我在她发高热说胡话的时候知道的。
当时以为只是她年纪小,一厢情愿。
而今,我想起她白日里在舞台上的惊鸿一现,心中隐隐有了不悦。
入夜,我和衣就寝,烛光映衬下,陆照珩的眉眼格外清俊。
这是小产后我们第一次同房。
他喝了点暖身酒,指尖贴在我滚烫的肌肤上摩挲游移,口中喃喃念着“阿云,阿云。”
可他尝试了数次,直到伏在我身上微微冒汗,始终没能成功。
我意兴阑珊地推开他,“夫君今日累了,还是别试了。”
陆照珩有些赌气似的将我翻过身。
“不行,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,你莫动……”
我却拉过了锦衾,遮掩住一身暧昧红痕。
“按照规矩,我身子养好,妹妹也应离开侯府了,灿月到底还是个云英未嫁的姑娘,岂能久居外宅?”
他愣了一下,随即垂眸。
“自然,都依夫人说的办。”
一夜无风无月。
我吩咐下去这道逐客令后,沈灿月果然不声不吭地收拾了行李,不辞而别。
那几日,陆照珩都无甚太大的反应,我心中的疑虑也逐渐消散。
直到某个下午,我陪着陆照珩在书房研墨,府卫突然慌里慌张前来禀报:
“不好了,沈二小姐在门口磕破了脑袋,晕厥过去了!”
3
我握着徽墨的手一抖,墨汁径自溅到了衣裙上,洇染了点点墨花。
陆照珩脸上闪过明显的慌乱。
“怎么回事?她不是已经回尚书府了吗?”
“沈二小姐来的时候,只穿了一件单衣,自称她对不起侯爷和夫人,嬷嬷们已经把她扶到西暖阁了。”
沈灿月昏迷了半个时辰,头上包扎的伤口都在渗血。
这期间,我和陆照珩一直临窗而立,彼此无言。
郎中赶过来时,她刚好醒了过来。
“恭喜侯爷,这位贵主子是早孕脉象,已经有一个多月身孕了!”
一个多月……而沈灿月之前两个月,都是在侯府后院住,能接触的唯一男子,便是陆照珩。
我身形微晃,没能站稳。
是侯府的小侍卫及时伸手扶住了我,低声道:“夫人当心足下。”
而沈灿月呆呆地倚靠在床边,小脸惨白,连哭声都在发颤。
“姐姐,是我对不起你,那一晚姐夫喝醉了,我扶他回房中,是我亵渎了他,跟姐夫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这时,在旁边沉默已久的陆照珩突然开口:
“灿月!别说了。”
他转头定定地看向我。
“一人做事一人当,灿月腹中孩子的确是我的。阿云,是我对不住你。”
看着他们彼此隐忍深情的模样,我捏紧了袖口,忽然有些可笑。
其实我也很纳闷,郎中说我的身体并无问题,我七年来喝了那么多坐胎药,都难以怀上。
好不容易怀孕,如此精心地养着,也没能保住。
她是如何在来府上短短两个月不到就遇喜的?
沈灿月悲戚地拽住我的衣袖,紧抿下唇。
“我痴情于侯爷,已经抛下了礼义廉耻,只求给腹中孩子一个名分……灿月愿意嫁给姐夫,哪怕是妾。”
她看似是在求我,可我发现她的眼神,分明势在必得。
我挥挥手让陆照珩离开,有些体己话需要我们姐妹俩共同说开。
他有些犹豫,我冷笑,“怎么,还怕我害了你的孩子和小情人不成?”
陆照珩终于掀帘离开。
偌大的暖阁内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我冷冷盯着沈灿月,“他走了,不必再演戏了,说吧,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?”
沈灿月果然收起了眼泪。
她几乎嗤之以鼻地笑出声来。
“姐姐,你已年近三十,还无法为侯爷传宗接代,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断子绝孙,侯爷这般清俊非凡的男子,他值得拥有许多女人前赴后继为他生孩子。”
我默然闭目。
这些字眼都太过刺耳,成为横亘在我和陆照珩多年感情里的一道坎。
让这段原本纯粹的感情早已变得浑浊不堪。
“至于我,灿月还能奢望什么?自从偷听到你与爹爹交谈,要把我嫁给区区五品官员为妻,我已经对你们死心了。”
“同样是爹爹的女儿,凭什么你能当尊贵无比的侯府夫人,我却只能当小小官员之妻?”
沈灿月珍惜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,一字一句道:
“姐姐,我与你不同,你生来就是贵女,可我的人生,只能靠我自己来努力争取。”
我静静听了许久,望着窗框上的斜阳花影,忽然笑了。
“原来妹妹看上的,是我这侯府夫人的宝座。”
“只是你大约赌错了人,这个男人,真的值得你我托付终生吗?”
沈灿月嚣张的笑容有些凝滞。
“你什么意思?是不肯放手吗?”
我没有回答她,转身慢慢离去。
走到门口时,终于难以抑制地扶住门框。
心脏蚀骨般的抽痛袭来,毒性在发作。
我曾经和沈灿月一样,天真地相信情爱,将自己的未来被动地交给了一个男人身上,等待着被救赎。
可后来我才明白,这行为本身就愚蠢至极。
我回屋去的时候,陆照珩正在我房中来回踱步,显然等了很久。
他涨红了脸,急忙跟我解释:
“阿云,我知道我说什么现在都无济于事,可是那次她迷晕了我,我们就有了一次……”
“真的只有一次?”
我打断他,认真地抚上他皱起的眉头。
“夫君,你知道吗?你每一次说谎都会皱眉头。”
原来,在我为他滑胎小产的那个月,他白日里照顾失子之痛的我,晚上就在小姨的房中寻欢作乐。
“到底要怎样你才肯相信我?你告诉我,我该怎么办。”
陆照珩伸手握住我的手指,纤长的眼尾隐隐泛红。
“不重要了。”
我平静地看着他,眼中无波无澜:
“陆照珩,我们和离吧。”
4
陆照珩似乎不想面对,他身形瞬间紧绷,声音也越来越低。
“阿云,我,我知道你一时无法接受,但到底是我的孩子,我们彼此都……先冷静一下。”
一向能在朝堂上舌战群儒的小侯爷,这般结巴,实属难得。
可他不知道,七年来我已经没有比此刻更加冷静的决定。
在我们冷战期间,远居外宅的老夫人已经得知了沈灿月怀孕的消息,大喜过望,直接接了沈灿月过去住。
很快,老夫人就和我父亲做主,称我失德,不孝有三无后为大,犯了七出之罪,择日就要迎庶妹入府为妾。
陆照珩没有反对。
纠缠数日,他一直躲在外面办公差,不肯回来。
小侯爷要纳妾的消息,传遍大街小巷。
他终于肯再来见我。
陆照珩想要握住我的手,却被我躲开,伸出的手停留在空气中,倒显得十分伤情。
我不声不吭,拿出了早已替他拟好的休书。
“签好了这休书,你放我自由,我也还你清净,从此男婚女嫁互不相干。”
陆照珩看都没看休书一眼,只疲惫地揉了揉眉心,半晌,默默垂下了头。
“阿云,我也是需要传宗接代的。”
我忽然感到一阵可笑。
七年了,年少情深,也终究敌不过这冰凉的四个字,传宗接代。
“孩子生下来交给你带,至于你妹妹,就把她扔到外面宅子里养着,就当养条阿猫阿狗了,我们还像从前一样,好不好?”
他近乎恳求,我却讽刺回应。
“你就这样对待为你生孩子的女子,可见无论于我,还是沈灿月,都是负心人。”
“我只想要和离,若你不肯签字,我自己去书房寻你的私印便是。”
我转头要离开,陆照珩却在冷的夜风中突然抱住我,从背后环住我的腰身,紧紧的。
仿佛在拼命抓住风筝的线,害怕随时失控飞走。
“阿云,我不许你离开我。”
我轻笑,“当初你我成婚时,彼此立下此生一双人的承诺,如今契约既毁,我为你腾空,正好迎妹妹为正室,有何不好?”
陆照珩却仿佛什么都听不进去。
男人总是这样,既要也要,满嘴荒唐誓,半点也做不得数。
他一个打横将我抱起,在我的惊呼下,径直将我推到了床上。
他边解腰带,边红着眼喘息:“上次未和夫人完成的周公之礼,今晚合该补上。”
我安静地看着他,既熟悉又陌生。
正如无数个春情摇动的夜,我深深迷恋着这双眼睛。
现在里面只剩下满目荒芜,他与我,都无半分情欲。
腰间系带被暴躁地抽开,陆照珩准备吻过来时,我伸出颤抖的手臂。
“砰!”
床头的邢窑白瓷应声而碎。
我声音颤抖,将碎瓷抵在了他脖颈,锋利的瓷片划破了他的皮肤。
猩红蜿蜒流下,滴在了我的眉心,是他的血。
“你如果再碰我,我马上杀了你,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。”
陆照珩猛然怔住了,显然没有料到我如此激愤。
那是昔日一起南下江南时,他到官窑里亲自为我烧制的瓷器,还篆刻着我的名字,我一直视作珍宝。
他曾牵着我的手,指天发誓:
“我陆照珩,此生只有沈轻云一个妻子,你我之间没有和离,只有丧偶。”
可我们终究是走到了反目成仇的这一步。
这时,门口的小侍卫听到动静闯了进来,警惕地拉开陆照珩。
“侯爷,请自重。”
他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近卫,只对我忠心耿耿。
陆照珩终于没有再继续下去。
他悲愤地捂住自己的伤口,踉跄退后了几步。
“阿云,我可以给你休书,但你记住,离开了侯府,你什么也不是。”
在他愤而转身出门的那一刻,我扶着床檐,猛然吐出了一口黑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