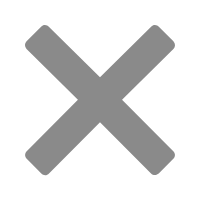-
有糖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第一章
哥哥出海打渔,带回来一个漂亮的鲛女。
那女人肌肤雪白,上半身赤裸,身下波光粼粼,泛闪着淡蓝色鱼鳞。
“夭夭,等给她剥了皮,哥哥给你做一条流仙裙好不好?”
可到了夜里,我看到哥哥逼人鱼跪在他面前,发出奇异又欢愉的声音。
直到后来,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也长出了鳞片。
1、
深夜,哥哥披着蓑衣捕鱼回来了。
他面色疲惫,可眼睛却亮亮的,手中拖着一个麻袋,笑着说:
“夭夭,我们要发财了。”
我赶紧上前替他接过来,可当我拖过那个敞口的麻袋,里面沉重的东西把我吓了一跳。
“哥,你捕到人鱼了?”
我们村叫鲛珠村,自古就有捕猎人鱼的传统。
人鱼全身都是宝,他们织的布名曰鲛绡,轻盈如月光浮动,一匹千金。流下的眼泪是稀世鲛珠,专供皇家御用。
用人鱼的脂肪熬制的蜡油,千年不灭;剥下来的皮和鱼鳞可做流仙裙,甚至鱼骨能入药,包治百病。
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是村里最好的捕鱼人,几乎每年都能猎到人鱼。
这份手艺传给了我爹,我爹瘸了腿之后,又传到了哥哥手里,只不过,随着人类的过度捕捞,人鱼越来越少了,已经五年没有捕到过。
我家的光景也衰落了。
这也是哥哥二十多岁,至今还没有讨上媳妇的原因。
人鱼制品的市价日渐攀升,已经到了价值万金的地步。
而哥哥捕回来的这条雌性人鱼,长得非常美。
虽然还在昏迷,可她有着一双摄人心魄的漂亮眼睛,杨柳细腰,上身却饱满异常,樱桃似的红唇一张一合。
长发紧贴在她雪白的肌肤上,双臂似乎在发冷,抱在轻轻颤动的酥胸前。
她们会织鲛绡,可这条人鱼被我哥带回来时,浑身赤裸,皮肤还布满了淤青。
我有些纳闷,这么漂亮的人鱼,怎么在海里不穿衣服呢?
爹娘很快闻声赶过来了。
他们看着被我哥关进铁笼里的鲛女,十分高兴,决定明早就给她剥皮,起锅熬油。
“我的好儿子,你终于出息了,这下我们家的光景就好过了,真是光耀门楣!”
但是被我哥急切地制止了。
“我自己亲手捕来的人鱼,只有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处置。”
“况且她这么瘦,就算现在熬油也熬不了多少,还不如先收集点鲛珠,等养肥了再剥,也不迟。”
爹娘面面相觑,觉得有道理,便都乐呵呵回屋继续睡觉了。
哥哥扭头对我道:
“夭夭,快去睡觉,等到时候宰了这人鱼,哥哥把她的皮剥下来,给你做一条流仙裙怎么样?”
我头皮发麻,看着受伤的人鱼,摇了摇头。
“哥,我不要裙子,只要能帮家里改善生活就好。”
那天夜里,我缩在自己的小茅屋里,怎么也睡不着。
我突然很想去看看白天那条漂亮的人鱼。
于是,我蹑手蹑脚来到了关她的柴房,发现铁笼里面空荡荡的。
我刚想大叫人鱼跑了,这时,却看到对面哥哥的屋子还亮着昏黄的光。
我悄悄走过去,听到里面传出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
2
“呜——”
狭窄逼仄的屋子里,传出了女子难受的声音和铁链晃动的响声。
我心惊胆战地透过虚掩的门向里望去。
那条人鱼依旧不着寸缕,雌性人鱼的身形比较娇小,她几乎埋在了哥哥高大的阴影里。
哥哥背对着房门,任由人鱼跪在床上。
人鱼十分痛苦,脖子上拴着铁链,却仿佛被什么堵住了嘴,只能发出些呜呜的闷哼。
一柱香的时间后,哥哥结束了。
他满足地眯起眼睛,信手在人鱼娇嫩的身上又掐了一把。
“真是个尤物,可惜没有腿,白璧微瑕了。”
我不知道哥哥在干什么,只感到害怕,因为屋子里落了一地的鲛珠,是那人鱼流的眼泪。
第二天,哥哥又在同一个海湾捕回来了另一条人鱼,全家人都欣喜若狂。
只不过,这一条就没有上次那个鲛女那么幸运了,爹娘决定尽快宰杀了他卖钱。
这是一条雄性人鱼,年纪似乎不大,鱼鳞也没有那么闪闪发光,当晚就被剥了皮,抽去筋骨。
他的惨叫和挣扎声持续了半夜,才被爹和哥哥两个人摁住,彻底没了动静。
“桃夭,愣在那里干什么,还不快来搭把手!”
我爹累得满头大汗,叫我进去帮忙烧柴火。
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宰杀人鱼,震撼与恐惧难以言表。
血一直蜿蜒流淌到了屋子外面,刺鼻的血腥味盈室。
地上掉落下来两颗空洞无神的眼珠,还有一地形状怪异的鲛珠。
那名雄性鲛人的头颅被悬挂在墙上,似是胜利的旗帜。
一块块带着雪白脂肪的人鱼肉被分割成块,脂肪层被削下来扔入沸腾的锅中炼油,很快在娘的搅拌下,炼成了一锅如雪般纯净、滑腻的人鱼油。
空气中蔓延着一种甜腻的异香,与腥味混合在一起。
哥哥笑得眼睛眯起,鼻翼两侧的雀斑兴奋地一股一股。
“夭夭,今晚上我们吃一顿人鱼宴,这人鱼肉可是延年益寿的好东西呢!”
他们忙忙碌碌做了一大桌子人鱼肉做的菜,盘子里盛满了白花花的油脂,如三头饕餮般,狼吞虎咽地吃着。
而我谎称受了风寒没胃口,一口都没吃。
翌日,周围村民以为我家在杀人,有人还报了官。
结果官兵找上来之后,我爹只是收拾东西,跟着去了趟衙门,不仅很快就被无罪释放,还带回了满满一箱金银珠宝。
他眉开眼笑地说,他把人鱼皮和蜡油卖给了他们,虽然不是上品,但物以稀为贵,还是卖了高价。
城里的达官贵人最喜欢这好东西。
我心里十分不舒服,可娘告诉我,千百年来鲛珠村都以此为生,杀鲛人,和捕杀其他鱼都一样,并没有区别。
那一晚,关在柴房的鲛女发出凄厉的哭声。
原来,那天哥哥捕杀的雄性鲛人是她的弟弟。
人鱼开始不吃不喝了,每天在铁笼里伤心欲绝。
爹娘急了,这样下去她的鳞片和皮相都会受损,自然就卖不上好价钱了。
娘让我去给她喂饭。
“你是小女儿家,人鱼对你不会防范,你好好劝她,让她多少吃点东西。”
我用海藻和扇贝做了他们喜欢的食物,绞尽脑汁摆好了盘,递给笼子里的人鱼。
她仍然背对着我,一言不发。
我好言相劝:“你还是吃点吧,如果你绝食,我爹他们只会宰你宰的更快。”
“我不会吃你们的食物的。”
我急了,“你不吃,我哥说会给你点颜色瞧瞧,我这关是最温柔的了!你可要想清楚。”
那人鱼终于扭过头来,雪亮清透的月蓝色眼睛看向我。
下一瞬,她露出了惊愕的神情。
不知道为什么,那眼神看得我很不舒服。
“你,你不吃就算了。”
我索性站起来,在我即将转头离开时,一只玉臂轻轻拉住了我的手。
“小姑娘。”
3
“要吃糖吗?”
说着,人鱼摊开手掌心,露出一颗晶莹剔透的淡红色糖果。
在这个小渔村,糖是稀罕物,只有城里的有钱人才能吃到,我也不过逢年过节才能吃到哥哥买回来的粽子糖。
阿爹说过,人鱼最擅蛊惑人心,她不过是看我是小孩,拿糖想诱引我罢了。
我摇了摇头。
“你是不是想逃跑?不要耍什么花招了,我爹娘不会放你走的。”
人鱼叹了口气。
“我只是看到你,想起了家里年幼的妹妹,有些想家了,你若是不信我也罢了。”
我心跳砰砰。
“我承认你长得的确很漂亮,可我们家以捕人鱼为生,放走你,我们的生计就不能维持了。”
我又赶紧补充了一句。
“不过我会想办法尽量说服阿爹,让你生产鲛珠就好,不要害你。”
她遗憾地收起了糖果,说看在我对她这么好的份上,想告诉我一个秘密。
我假装生气,没好气地把盘子放到地上。
“什么啊,除非你好好吃饭,我就听。”
人鱼果然乖乖吃饭了,她一边小口小口吃着,一边说:
“其实,这还不算最好吃的糖。”
“我知道一种糖,是用月光草做的,那才是人间美味。那种月光草,长在月光下的海边沙滩上,将秸秆含在嘴里,甜丝丝,像海水一样的微凉。”
我沉默了,我没见过月光草。
爹娘说海边危险,我体弱,所以从来不允许我触碰海水。
可人鱼对甜味的描述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
我嗜甜如命,但糖价贵,家境贫寒的我从来没有奢望过。
那天夜里,我还是趁夜溜出家门,去到了海边沙滩上。
那儿果然如人鱼说的一样,长满了摇曳着银白色叶片的月光草。
这些白天根本看不见的植株,在空寂无人的夜晚,静悄悄在沙滩上摇晃。
我鬼使神差地上前,摘下了一根月光草,将秸秆放进了嘴里。
一种奇异的清甜充斥着口腔。
以至于好吃到我忘记吐出来,咕咚一下将糖水咽了下去。
我慌慌张张丢掉秸秆,跑回了家中。
那甜美的味道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,越记越深。
吃下月光草的第二天,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
因为第二天早上,我在自己的手腕上发现,一小片皮肤竟然开始长出了鳞片。
那是一片淡紫色的细小鱼鳞,泛着美丽的蓝紫微光,却把我吓坏了。
爹娘很少对我生气,但想到他们罕见生气的样子,我害怕起来。
一定是那人鱼干的,月光草有毒!
当我生气地去找铁笼里的人鱼理论,质问她为什么要害我时。
她却仿佛预料之中,凄冷地笑了。
“小傻瓜,你本就是人鱼啊,我们本是最亲的同胞,你却被他们哄骗,还在助纣为虐,殊不知他们养着你,下一个要剥皮抽筋的就是你……”
我震惊地踉跄了几步,不停地摇头。
“你瞎说!”
爹娘对待人鱼就像宰杀的畜牲一样,拔鳞,扒皮,剔骨,干脆不留情。
人人都夸我家心善,在这个重男轻女的村子,大多数女孩生下来都是在尿壶里被溺死的命运。
可爹娘却把我捡回了家,还好吃好喝养着,有哥哥疼我,从不让我干粗活。
我觉得我是整个鲛珠村最幸福的人。
我怎么可能是人鱼呢?
4
我跑回屋里,用宽大的衣袖遮住了自己的手腕,希望毒素自己能消解掉。
路过堂屋时,我看到墙上挂着眼窝空洞的人鱼头颅,还有血淋淋的鱼尾巴,不禁打了个哆嗦。
晚上,哥哥喝得醉醺醺,从城里回来了。
自从有了些钱,他成日都去城里逛花楼,在赌坊间流连。
“钱输光了,再让那条贱鱼哭一哭,给老子哭一堆鲛珠出来,明天我肯定能赢回来。”
到了夜里,哥哥又去折磨人鱼了。
如往常一样,屋子里发出痛苦和欢愉交织的声音。
这次持续了整整半个时辰,我听到哥哥拿鞭子抽打人鱼。
我知道,他是为了让人鱼哭泣,获取更多的鲛珠。
然而在哥哥走后,没想到,我爹也趁我娘熟睡,一瘸一拐地钻进了柴房。
他进去的时候,满脸通红,是提着一杆烟枪去的。
里面鲛女的叫声更加凄厉了几分。
声音绝望,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我按了按心口,一种莫名的悲凉涌上心头,我这是怎么了?
夏日闷热,我有睡前沐浴的习惯。
就在我泡完澡之后,擦拭身体时,我从双腿间擦出了一抹殷红的血迹。
原来是自己第一次来了癸水,我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
娘说女子到了年纪就会来癸水,有了这个才能嫁人生子,是变成女人的象征,因此我提前就有心理准备。
那人鱼果然是胡说的,明明只有人类女子才会来癸水。
我今年及笄,身子发育得越发好了,但我性情保守,总是用束胸布偷偷束起来。
此刻,我站在铜镜前,摘掉了那些紧箍咒般的布条,一对饱满的雪胸再也束缚不住,莹白如玉。
这时,我突然发现镜子里有一张人脸,正透过门缝往里瞧。
我惊呼一声,低低地捂住胸口。
“谁在那里?”
我哥推开门走了进来,笑眯眯的目光添了几分深沉。
“别叫,是我,哥来拿点东西。”
他说这话时,眼神仍然在我赤裸的娇躯上上下下打量着。
“哥,你进屋怎么不敲门啊,吓我一跳。”
跟哥哥四目相视,我的脸顿时烧得滚烫。
虽然从小时候就被哥哥亲自洗澡,哄我睡觉,但现在大了,男女授受不亲,多少还是感到不自在。
“夭夭长大了,马上就是大姑娘了。”
哥哥笑着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,进屋取走了他的东西,就离开了。
得知我来了癸水后,娘亲十分欢喜,还特意去市集买了一匹红绸布,说要给我裁新衣裳。
可我总觉得心里有些怪怪的。
我没敢把手腕上长鱼鳞的事跟任何人提起。
那片小小的鱼鳞也像一根刺,扎在我的心上。
这天收拾碗筷时,我把碗端去后院清洗,无意中听到爹娘在灶房聊天。
两人都刻意压低了声音,可我还是断断续续听到了几句。
有什么“一个月后”“受孕”“吃闲饭的赔钱货”等字眼。
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
“等了十年,终于准备养成了!”
“夭夭还有一个月就及笄了,他们的婚事也该操办起来了,现在这副身子养得珠圆玉润,是最好的名器。”
阿娘顿了顿,语气透着几分得意。
“她的皮子,得现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