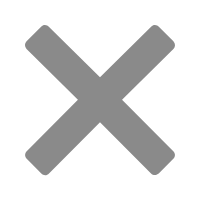-
有糖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1
我曾陪他从落魄皇子,走到万人之上。
新帝登基,论功行赏,却命令我为贵妃火中取栗。
紧接着,我全族覆灭,我成了永久的太子妃,也失去了最后一点利用价值,
呕血过后,我忘却了所有跟他的前尘过往,他却疯了,竟一夜白头。
皇宫大火,我冷眼跳入大火,以命换命,只为求得我原谅。
呵,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
大火中,我平静拉着他的手。
“凡是过往,皆为耻辱。”
1
我醒来的那一天,正逢贵妃娘娘被册封为皇贵妃,皇宫上下,无不风光。
而我在冷宫苟延残喘。
浑身上下都是被火灼伤留下的疤。
本该陪在贵妃身边享无上尊荣的陛下。
却在这一天。
一脚踹开了冷宫破旧的门。
那木门嘎吱,砰的一声,不堪重负倒下!
灰尘四扬。
就在上一秒,邢娘还宽慰我说。
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
她说奴婢已禀报陛下,陛下不会坐视不管,毕竟我曾经对陛下……掏心掏肺。
我很疼,却又茫然。
邢娘看我的眼神,小心翼翼问我。
“娘娘真的忘了陛下吗?”
我尚未来得及回答,嘴巴慢慢吃惊地张开。
天子当真是天子,与寻常人不同。
一身骄矜,衣绣云纹。
合该高攀不起。
“温飞月!”
他大步走上前,隐忍怒意,深不可测,那双修长青筋的手,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
不怒反笑。
“你又在玩什么把戏?”
“失忆?偏偏挑皇贵妃册封这一天,你可真会挑日子。”
被火炙烤过的地方,很痛,太医草草包扎好的伤口又渗出血。
我险些疼出眼泪,却不敢哭。
他是天子。
连那双手都养尊处优,如羊脂玉。
但为何会有薄茧,好似早年历经风霜?
我不知晓。
却深刻记着陛下的残忍无情,喜怒无常。
立刻挣扎着跪在地上。
在徐敬风几分惊疑错愕的目光中。
恭谨微小的跪拜。
“陛下金安。”
冷宫只有几颗枯败的枇杷树,落叶飘落一地,风从破旧的纸窗钻进来,发出呜呜地声响。
我衣衫单薄,面容苍白。
青丝滑落在地。
气氛静到能听到人的呼吸声。
陛下的脸面无表情。
他看过邢娘,薄唇轻扯,却冷的让人战栗。
“这就是你说的失忆?”
邢娘怦然跪在地上。
“不是的!陛下——”
“看来这场大火倒是成全了你争宠的心思。”陛下的声音如迎寒冰,薄情莫测,从我的头顶砸下来。
“温飞月,你死了这条心。”
“你真以为你曾经的微薄相助值几分?这辈子,你也比不过皇贵妃!”
陛下拂袖而去。
只有邢娘尚未说话的话,卡在喉咙眼里。
娘娘她真的失忆了。
她只是……把你们那段曾在落魄时艰难共处,琴瑟和鸣的日子忘掉了。
2
冷宫实在阴寒,伤势不易痊愈,邢娘劝我出去晒晒太阳。
我便同意了。
我不能走出冷宫,好歹能在后院挑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坐下。
假山后面有人在唠嗑。
“堂堂太子妃,依仗着父兄在边疆手握重兵,竟敢下毒加害淑贵妃,被打入冷宫,真是活该!”
“这次梨花轩走水,可怜陛下愣是看都没看她一眼,一心救皇贵妃。”
“真以为她父兄还是曾经……”
假山后面的人,肆无忌惮大声喧哗。
“谁在那里胡说八道,敢胆议论太子妃,给我出来!”邢娘大喊。
没有一个人出来,只听见唰唰唰的跑步声。
邢娘愤怒叫住她们,是两个嘴碎的宫女。
她们梗着脖子,看过我,不屑道。
“还太子妃呢。跟着陛下幽州苦寒五载,连个天地都没拜,无名无分,陛下也不在意,宫中谁敬她半分?”
“你!”邢娘气得脸红脖子粗,还是我拉住她,摇摇头,说算了。
那宫女嗤笑:“瞧见没,她都比你一个奴婢有自知之明。”
“娘娘,不要相信这帮奴才的鬼话!”邢娘红着眼,愤愤不平,“陛下从前还在幽州的时候,不是这样的……”
“好,我听你说腻歪啦。”我闭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,“那时候我们虽落魄,却相濡以沫。”
邢娘眼睛更红了。
我叹口气,摸着她的脸,低声说。
“你跟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娘娘,也是苦了你。”
“但那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,忘就忘吧,以免伤怀。只是有些想念父兄,可惜他们这辈子,也不能入京半步。”
先皇忌惮父亲手中的兵权,下令让他一生驻守边疆,无诏不得入京。
而我,从出生便孤身一人留在京城,作为皇家牵制父兄的棋子。
邢娘是打小看我长大的。
她张张嘴,欲言又止。
那两个宫女跑远,对视露出笑,绕了一圈回到延禧宫。
白彤萱正悠闲的躺在摇椅上,宫女殷勤向她汇报。
“奴婢的话都传到那个病秧子耳朵里,她已经瘦得没有人形,保证活不了多久。”
“不日,皇贵妃娘娘就能封后了呢!”
3
许是宫女的话勾起我思念家人的回忆,我回去一阵翻箱倒柜,才在陈旧的红木箱中翻出我娘一针一线给我绣的红嫁衣。
可惜,这辈子是没机会穿了。
我有些遗憾,手指摸过嫁衣上密密匝匝的针线,忍不住穿上试了一番,问邢娘好不好看。
“娘娘真美。”邢娘惊艳道。
美则美矣,当夜,我又病倒。
高烧来势汹汹,我穿着娘给我绣的嫁衣泪眼朦胧,好像家人就在身边。
邢娘慌不择路去请太医,却被告知。
贵妃娘娘头风发作,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在延禧宫。
那晚邢娘在延禧宫外跪了半宿,才请动皇上。
可她若知道接下来是何等光景,想来那夜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去延禧宫的。
陛下带着皇贵妃过来的时候,我正烧得糊涂,蜷缩在床榻上。
冷宫还漏着风,皇贵妃眉头一皱,巧目流转到我身上的红嫁衣,嫣然一笑,轻声细语却显软刀。
“听闻太子妃一场大火烧傻了,本宫还不信。如今看来,倒有几分真,怎地后位空悬,太子妃就连嫁衣都穿上了呢?”
陛下的目光同样落在我身上,微微一滞。
灯火昏黄,看不清人脸色。
我浑浑噩噩,听她一口一个太子妃。
陛下已经是陛下,只有我还停留在过去。
可我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的太子妃呢?
我也不记得。
但我记得入宫一年,如同噩梦。
我曾长跪在大雪隆冬的天,也是在陛下这样深沉薄凉的目光下,强忍着痛为贵妃火中取栗,十指连心,鲜血淋漓,搏美人一笑。
事后。
他一脚踹上我的心窝,将我踹飞到冰冷刺骨的河水中,连声音都寡淡冷漠:“别脏了贵妃的眼。”
那天回去,我疼了很长很长时间。
但我没资格委屈。
陛下乃是天子,江山尽在脚下。
遑论一个女子。
君要臣死,臣也不得不死。
父兄一生镇守边疆,不肯归京,以表忠心,我不能给父兄惹麻烦。
“脱了。”
陛下眉骨轻抬,浓墨重彩的深邃,隐匿在阴影中。
声音不高不低。
力道砸落心尖。
4
邢娘惨白着脸跪在地上,不住磕头。
“陛下,都是奴婢的错!娘娘她只是太思念家人了,这衣裳是夫人当初亲手为娘娘绣的,这才留个念想!”
“哦?”白彤萱语气慵懒。
“你的意思是说,整个将军府都依仗着太子妃曾有恩于陛下,挟恩上位,盼望着太子妃当皇后咯?”
“砰!”
邢娘被陛下一脚踹翻,像断了线的风筝,头磕在桌角,汩汩流出血。
陛下眉眼暴戾深重。
“有你说话的份?”
“邢娘!”我嗓音沙哑干涩的不行,尖叫一声,颤抖爬下地,扶起邢娘单薄的身体,死死咬住唇,尝到了铜锈味。
一字一顿。
“飞月自知德不配位,在皇贵妃面前自惭形秽。”
“我不想当皇后,也从来无恩于陛下!”
于陛下而言,他从不愿提起从前,登基后更是恣睢阴郁,违者杀无赦。
或许落魄时的记忆,被他痛恨为耻辱。
于是连我,也一并被他视作耻辱。
可我并不在意。
天子不愿,那便埋葬。
“太子妃竟如此善解人意?”白彤萱凉凉笑道,摆弄着精致的长指甲,华冠丽服,咄咄逼人。
“想来幽州五载也是传闻?”
我紧咬着牙,信誓旦旦。
“飞月只愿陛下和皇贵妃天长地久,永结同心!”
“凡是恩情,微不足道,皆为过往。飞月惶恐,万万不敢当。”
说话的时候,我感到陛下的目光沉沉落在我身上。
莫测莫辨,喜怒无常。
让我浑身颤栗,连骨头都泛着疼。
“既是如此……”白彤萱娇嗔对陛下说道。
“太子妃这身衣裳实在僭越,大逆不道,不若就烧了吧。”
“不要!”
我喉咙惊愕嘶哑,逼出一声叫喊。
千恨万恨自己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拿出来,为什么还不够谨小慎微!
我终于抬头,惶然看着陛下,手指紧紧攥着他的衣摆,指骨苍白颤抖,哀求。
“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东西,我没有别的心思,我不想当皇后,求你,求陛下……”
灯下看人,更添三分颜色。
陛下眉眼俊美无双。
连玄裳云纹都彰显着高高在上的尊贵。
何曾几时也落魄不堪过,他会记得吗?
此时与我,云泥之别。
便长相绝。
“怎么入宫一年的礼仪,太子妃还没学会。”
沉冷平静的声音徐徐落下,徐敬风冷眼扫过去。
对上我近乎乞求的眼。
他大拇指摩挲过玉扳指,轻描淡写的示意宫女上前。
“嫁衣处置了,别再让朕看见。”
“是。”
“不要!!”
宫女上前扒我的衣服,太监还在旁侍候着,邢娘拼命拦着我,哀求着,血流着一脸!
我毫无尊严,泪流满面,只能拼命护着嫁衣,护着我娘的念想:“我脱就是了!你们别动手,我求你们……”
白彤萱居高临下上前。
混乱中。
“撕拉——”一声。
满地红绸碎裂!
好像母亲笑着的脸,那灯下咳血绣着的一针一线,绣满心血和期许,也碎裂在我面前。
“娘!”
我口中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,呆滞了好几秒,颤抖着想要捡起地上的残帛,手背却被白彤萱生生踩住,辗转。
而我衣不蔽体,在宫女太监的眼神中,人人耻笑。
“放手!”
陡然一声厉喝响起。
我晕死过去。
母亲在边疆不能入京,便在陛下登基之日,送了嫁衣给我,她常写信同我说。
我们飞月,将来要嫁一个心爱的男儿。
他不一定出身富贵,不一定才高八斗,但一定要用心待你。
哪怕是寒门子弟,也可厮守一生。
但现在,嫁衣碎了,我这一生,也不曾择上良人。
我爱陛下吗?
我只记得他的羞辱、厌恶、暴虐。
5
我半梦半醒,药香沉沉。
太医小心跪在地上,同徐敬风回禀。
“娘娘早年伤了身子,未能及时医治,沉疴难愈,又常服用避子汤,药性深寒,积淀成疾,恐难恢复如初啊。”
徐敬风背对着灯,一下下转着玉扳指。
他站在风口处。
视线落在我的脸上。
我身上盖着的,是陛下身上那件玄裳。
声音素来四平八稳,透着饮冰的薄凉。
“还有什么?”
“这场大火,太子妃确实烧坏了脑袋,她……可能忘记了一些事。”太医迟疑着说。
动作倏滞。
透过那扇纸窗,山脉连绵九万里。
是荒芜破败的幽州,民不聊生,寸草难生。
总有个女人,满脸笑脸,捧着药汤递到他面前。
声音甜糯。
“敬风哥哥,该喝药了。”
“敬风哥哥,我不苦。”
“我少时读过一句诗,金鳞本非池中物,一遇风云变化龙……敬风哥哥就是那一条龙,幽州困不住你的,一年两年哪怕十年也好,我们一定会回京!”
他们也曾同床共枕,也曾脉脉含情,在潦倒失意时滚烫。
恩情吗?
确实是有的。
药只有一碗,她从来不喝,也算金尊玉贵在京长大,却夜夜守着炉灶小心熬药,呛成花猫脸。
他曾问她值不值得。
她垂眸浅笑。
“当年我落水,只有三皇子不顾性命安危跳河救我,不为飞月身份敏感而疏远我。从那日起,飞月心中有您。”
“你还记得。”他当时声音平淡晦涩难明。
“飞月当然记得。”
“有些事,不必记得。”他惫懒轻声,云淡风轻转了话意。
确实,不必相记。
嗤笑声落下。
“柳长林,你在宫中数载,也能被她唬住?”
徐敬风声音便添几分讽刺。
“她就算忘了自己叫什么,也不会忘记过去!”
“无非是不甘于此,白费功夫罢了。”
他没忘的东西。
她更不可能忘!
就是没忘,才痛恨,疏远,相互折磨。
太医下句话停在喉中。
太子妃也许,没几年活头了……
徐敬风负手离去,背影挺拔清沉,也深陷风云诡谲的权重欲望中。
“那件嫁衣……同她身上盖的那件,一起烧了吧。”
6
嫁衣碎了一地,我哭了一天又一天。
听说陛下回去后感染了风寒,一连半个月没在后宫露面。
许是怕我烂在这个秋天,他大发慈悲的送给我一只狸花猫。
我起初嫌弃它丑,对它总是爱搭不理。
当有一只硕大的老鼠爬上梳妆台,小小的它纵身一跃,直接摁住!
从此我对狸花猫刮目相看。
渐渐地也习惯了它栖息在身畔,给它起名叫豆花。
但一日清晨,不知怎么豆花上吐下泻个不停。
我急得不行,刚冲出大门就被门口的两个佩刀侍卫拦住。
”皇上有令,没有他的允许,娘娘不得私自踏出冷宫半步!”
”我的猫生病了,我要去请太医!让开!”
我板起脸的样子竟有些吓人,目光是烈的,毕竟流着边塞的血。
两个佩刀侍卫竟愣了一瞬,反应过来之后亮刀警告。
”娘娘休要再胡闹,容卑职禀告皇上再做决定。”
禀告禀告……等徐敬风来黄花菜都凉了!
他总是知道的最晚。
我给了邢娘一个眼神,纠缠住他们,邢娘立刻抱着猫狂奔出去!
”这……快去请皇上。”
我没想到,我先等来的不是徐敬风的责问,而是奄奄一息的邢娘。
她身上的伤鲜血淋漓,血肉模糊。
7
在宫女簇拥下缓缓走进冷宫的,是白彤萱。
”这个贱婢抱着猫冲撞了本宫,本宫赏她五十大板,不过分吧?”
我脑袋翁的一声炸开,一腔冰冷的火窜出心头,秋风吹不灭,满院荒芜。
声音沙哑。
”我到底还是太子妃,你凭什么动我的人?!”
“温飞月,太子妃这个位置,也不过是你苟且偷生偷来的!”
白彤萱语气骤然凌厉生厌:“陛下舍不得我陪他在幽州受苦,才不得已让你随行!”
我心口闷痛,一字一顿:“你以为一个太子妃,我稀罕?”
“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?”
白彤萱眯眸看着我,诧异一两秒,手抚步摇,但见云泥之别,嗤笑出声。
“真以为装个失忆就能让陛下顾念着往昔恩情?他迟迟不让你踏出冷宫半步,就是因为嫌恶你是个罪臣余孽!”
”你在说什么?”我盯着她,脑袋忽然很痛。
豆花和邢娘是为数不多能陪伴着我的家人,我害怕他们死掉。
对啊,家人。
父兄他们每年都会往京城送信。
但是今年,为什么一直没有信?
”娘娘,都是奴婢的错,奴婢甘愿受罚,您不要再听了!”
邢娘脸色煞白,后背还淌着血,挣扎着想要捂住我的耳朵,却被人一脚踹到膝盖,跪在地上。
”邢娘!”
我喝了一声,忍无可忍,抬手一巴掌狠狠甩在白彤萱的脸上!
豆花嘶吼地叫,瘦弱的小身板猛地朝白彤萱脸上扑去。
三道血痕在粉白的脸上格外扎眼!
拱着腰身的豆花,瞪着琥珀色的锐利眼睛,龇牙咧嘴,简直就是一只随时应战的小豹子。
其他人都没想到我竟敢动手。
一只病猫居然如此骁勇!
白彤萱尖叫着:“给本宫上前惩戒这个不受待见的罪女!”
场面一度混乱。
“陛下驾到!”
8
他刚下朝,戴冕冠,天子十二珠,黑色朝服。
“把猫带走。”
他冷漠命令。
“谁敢!”我挡在他面前,双目赤红。
“你敢抗旨?”徐敬风声音清清冷冷,那双眸分明晦涩的毫无温度,是一整个隆冬。
白彤萱捂着脸,委屈对徐敬风说:“陛下,你不能就这么放过温飞月!不把她杀了,难解心头之恨!”
“太子妃。”
徐敬风声音沉而漠然。
想来那把嗓子,从不会缱绻温言软语,开口必见血。
他看着我。
“舍不得猫,你来替它。”
五十大板。
一板一疼,血溅三尺。
染红了秋风荻花瑟瑟落。
我生生忍着痛,哆哆嗦嗦忍着,怀里死死抱着豆花,听邢娘跪在徐敬风脚边苦苦哀求,气若游丝。
“别求他……邢娘。”
打人的宫女是皇贵妃手底下的人,专挑狠的地方下手。
皇贵妃轻摇丝帕,笑意盈盈。
我满嘴是血,恍惚抓着陛下衣摆,在那骄矜清净的衣摆上攥出一个血掌印。
只问一句话。
”徐敬风,你让她说清楚……咳咳……我乃堂堂、堂堂将军之女,什么叫做我是罪臣余孽?!”
他没有停。
“娘娘!”
身后响起邢娘惊恐的叫声。
我呕出大片鲜血。
刚好四十九板。
徐敬风背对着我,僵硬扯扯嘴角,声音分明云淡风轻。
“继续打。”
9
听闻那日,是陛下把我抱回去的。
我昏昏沉沉,好像看到了徐敬风惊慌失措的脸。
分明在意无比,连手都颤抖。
恍惚,我好像看到了那个还是三皇子的徐敬风。
年少阴郁,眼角泪痣,眉眼漂亮的惊心动魄。
在荒凉潮湿的草屋里,我趴在他桌前逗他:“你笑笑嘛——”
幽州?
空白将我吞噬,如无边无际的海岸。
有人背对着我,雷霆大怒,指着太医说。
“太子妃死了,你们都得去陪葬!”
“娘娘醒了!”
有人惊呼,他转身看我。
幕帘重重,我看到了天子的脸,如在梦中。
迟疑着问。
“你是谁?”
短暂的寂静。
徐敬风紧绷的肩膀一瞬松懈下来。
冷笑出声。
“温飞月,装失忆的把戏你想玩几次?”
我大梦初醒,才记起来,原来是在宫中。
可是记忆中,那样破败贫瘠的地方,是在哪呢?
堂堂天子,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那样的地方。
又是我做梦了。
我死死攥住了他的手,要说什么。
没力气。
指尖滑落在天子腰间系着的香囊上。
针线分明粗糙陈旧,像戴了很久的模样。
徐敬风的视线顺着我的手滑落。
脸色微不自在。
他握住我的手腕,像是握住一截稍碰就折的枯木,眉头紧锁,声音冷冷。
“要不是皇贵妃不会缝香囊,朕也不会戴……”
“我的猫呢?”我嘶哑开口。
徐敬风脸色倏然更加阴沉骇人起来。
盯着我的脸。
“你只想问这个?”
我一阵心慌,嘴唇颤抖:“我……”
“没杀。”他冷冷道,“在冷宫。”
“那我父兄……”
“闭嘴!”
天子盛怒,长安城都要跟着颤一颤。
我一个哆嗦,松开手。
他似乎在等着我说一些其他的话,我抿唇良久,为使他快些离开,只好迎合道。
“能让陛下佩戴的香囊,定非出自寻常人之手,当然珍贵。”
徐敬风脸色微凝。
我绞尽脑汁:“日后,皇贵妃也会绣出更加珍贵的香囊。”
气氛静的落针可闻。
难道我说的不对吗?
徐敬风抬起了我的下巴。
四目相对。
我眸中泾渭分明。
他动了动唇。
“你当真不记得了?”
我眼中晃过茫然。
记得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