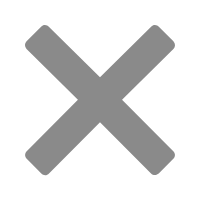-
有糖
本书由摸鱼看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1
婚礼泡汤了。
未婚夫和初恋旧情复燃。
他苦苦哀求:“苏清越,强扭的瓜不甜。”
“我宁愿过穷日子,也要和她在一起。”
我淡淡一笑,扔了他的行李,停掉他的黑卡。
几天后,一段视频冲上热搜。
夕阳西下,粉色寸头女孩被长发飘飘的男人紧紧箍在怀里。
一个精致如芭比,一个俊逸似神仙。
两人深情对望,吻在一起。
甜得人犯糖尿病。
未婚夫却后悔了,深夜打来电话:“苏清越,玩够了没?”
回他的男人笑得张扬:“我老婆有点忙,你哪位?”
1
婚纱照选片。
我纠结哪一张做电子请柬的封面。
发过去问薛少谦的意见,他迟迟没回复。
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消息:苏家赘婿与初恋旧情复燃,海滨酒店共度三天三夜。
我冷静点开标题,放大营销号曝出的图片。
沙滩上,我的未婚夫薛少谦,打横抱起一位穿着清凉的纤瘦美女。
女子似柔弱无骨,风姿潋滟,白玉似的手指捧着男人的俊脸。
某博服务器瞬间累瘫。
网友们比当事人还疯:
“赘婿不当了?泼天的富贵让我来接。”
“苏小姐看看我,我可比十八线小糊咖强多了,连屁股都比他翘。”
“不是下个月结婚吗?渣男竟在外面乱搞,婚礼还能举行吗?”
“心疼苏千金,支持姐姐独美。”
另一边,薛少谦的几个死忠粉开始蹦跶:
“男人婆终于被分手了,哥哥值得更好的。”
“有钱就了不起?霸占哥哥三年多,活该!”
“新嫂子是芭蕾舞者,可不是野蛮拳击手能比的。”
“恭喜哥哥,终于吃上好饭了。”
娱乐圈惯会炒作,我不想冤枉了薛少谦。
选片戛然而止。
拨通薛少谦的号码,传来的却是温声细语:
“苏小姐是吗?稍等,阿谦正在厨房给我煲汤。”
接着,我听到薛少谦的柔声责备,字字宠溺:
“嫣嫣,我的小祖宗,小心点。”
“不是不让你乱动,你跑下来做什么?”
一听我的名字,他的口气瞬间冰冷:
“她舔了整整三年,还真以为我爱上她了,做梦吧。”
“谁喜欢一身腱子肉的女人,想想都觉得恶心。”
突然的安静后,两人一起迸发出嗤笑声。
再开口时,女人的嗓音甜得发腻:
“阿谦,苏小姐对你情深义重,你会和她结婚吗?”
“说什么呢?不过是各取所需,和她过一辈子,我不如去死。”
“现在你回来了,婚约作废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
取下波波头假发,露出新染的粉色寸头。
脱掉洛丽塔甜裙,穿上宽松的运动装。
洗手盆中浮起一层白腻,看着镜子里的小麦色脸庞和凸起的肱二头肌。
抠下假睫毛,我笑了。
狗屁白幼瘦淑女,谁爱当谁当。
我可是金刚芭比,窈窕世无双。
2
三天后。
我在搏击馆练得满身大汗时。
薛少谦找来了。
他与苍白纤弱的女人十指紧扣。
她就是于嫣,清纯的小鹿眼,不安地忽闪着。
楚楚可怜的小白花,红色泪痣分外撩人,脚踝处还缠着绷带。
她紧紧贴在薛少谦身后,瞪着我手上的拳击手套,嘴巴呈现O型,早吓得花容失色。
薛少谦好像很害怕我欺负她,用一只胳膊挡在她的身侧,摆出保护的姿势。
我怒吼一声,冲空气做了两个凶狠的搏击动作。
于嫣钻进薛少谦怀里,轻声尖叫起来。
我咬住脖子里的满钻豹头项链,哈哈大笑。
锻炼的人围观看热闹,有几个还是圈里的朋友。
一阵诡异的安静后。
薛少谦牵着于嫣走到我跟前,声音有些战战兢兢:“苏清越,强扭的瓜不甜。”
“现在嫣嫣回来了,谁也别想再把我们分开。”
我褪下拳击手套,用毛巾擦着汗,语气淡然提醒他:“你想清楚了,失去苏家这个靠山,你在娱乐圈能混下去?”
薛少谦和于嫣甜蜜对视,斩钉截铁道:“我宁愿过穷日子,也要和她在一起。”
“我心里只有她,容不下别人。”
“余生,我会努力工作,好好补偿嫣嫣。”
薛少谦眼信誓旦旦,把于嫣往怀里带了带,温柔地抚着她的发顶。
这场面太美,我都被感动了。
呷了一口温水,平静地望着他们,我一言不发。
看客们按捺不住,纷纷对我侧目,为这对苦命鸳鸯鸣不平。
“听说,他们当初是被苏清越硬生生拆散的。”
“圈子里最刁蛮无理的千金,让于嫣消失了两年。”
“苏小姐高调追薛公子,砸亿元力捧,可惜临到结婚,还是功亏一篑啊。”
在嘈杂的议论声中,我不疾不徐拿起手机,给助理下命令:
“撤回对薛少谦的所有投资,解约所有品牌合作。”
“把他的行李整理好,扔到别墅门口,停掉他的黑卡。”
“立刻发微,薛少谦和苏氏解除婚约,再无瓜葛。”
抬头时,薛少谦已松开于嫣的手,双肩微微颤抖,脸色煞白。
扣了电话,我若无其事向更衣室走去。
薛少谦却突然喊我的名字,清亮的嗓音带上一丝沙哑:
“苏清越,别以为离开你我就活不了,地球不是围着你转。”
“整天一身臭汗,加上蛇蝎心肠,你永远得不到男人的爱。”
我回头,微微一笑,云淡风轻道:
“哦。”
重拳打在棉花上,薛少谦眸里除了震惊,好像还有一丝不甘。
吃瓜群众又不淡定了:
“不对劲啊,薛公子是不是早就失宠了?”
“以前他但凡多看哪个女艺人一眼,苏小姐都要把人家封杀。”
“这次怎么不闹了?我还想拍段食人花大战小白莲的视频,说不定能火。”
“阿谦,我的脚好痛啊。”
美人蹙眉,向薛少谦张开双臂。
薛少谦赶紧抱住于嫣,弯下腰,捏住她的脚踝,满眼担忧。
看着他们的恩爱模样,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,密密匝匝地疼。
小明星我早就玩腻了。
最爱吃醋的那个人,怎么还不回来?
3
我在至尊VIP套房洗完澡,出来时人群已经散了。
偌大的训练馆里,静悄悄的。
只剩阿宇一个人在扫地。
一米八五男大校草,气质温文尔雅,怎么看都和打打杀杀的武馆不太搭。
可他偏偏是这儿的老板。
阿宇抬头望着我,半天才喃喃道:“越姐,你还好吗?”
“别听薛少谦瞎说。他为出名爬你的床,现在玩痴情人设,这戏子又当又立。”
“你是又飒又甜的公主,我们都爱你。”
“尤其是……琛哥。”
最后一句,阿宇说得小心翼翼。
好像生怕伤害到我,说完后,他眼眶红了。
两年来,那个名字成了说不出口的禁忌。
每每触碰,身心必然伤痕累累。
我摸了摸项链上的豹头,冲他干笑一声。
善良的小伙脸僵了一阵,继续安慰我:
“越姐,我有一种感觉,琛哥他并没有离开我们,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。”
“我娘说,只要心里思念一个人,无论在哪里,对方都能感受得到。”
我身体微微一滞,连带大脑也僵了几秒。
是吗?
那他一定能时时刻刻感知到我的想念。
直到阿宇离开很久,我还在回味那句话。
“他会回来的。”
我蜷缩在沙发上,脑海里那个人的影子越来越清晰。
不知不觉间,泪水汹涌而出:
“许以琛,你说过25岁娶我,骗子,你都26了,怎么还不来?”
“我今天训练时受伤了,好疼,你来给我擦药啊。”
“许以琛,你回来,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。呜呜呜……”
哭着哭着,我睡着了。
似乎有一双微凉的手为我擦干眼泪,耐心地给伤口消毒。
他勾着唇,轻声说:
“我的小豹子,有我照顾你,保证不让你留疤。”
我猛地睁开眼睛。
眼前却只是一片明晃晃的光。
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伤口一阵阵刺痛,内心空虚到颓丧。
我仿佛回到第一次见许以琛时。
5
上高中的第二天,我迎来人生至暗时刻,母亲去世了。
但还不够,在学校我遭遇严重的校园霸凌。
班花和小跟班把我骗到体育器材室。
锁上门,关了电闸。
我最怕黑了,在慌乱中弄倒铁架,一边哭喊,一边抚着伤口砸门。
绝望地抱着头,希望这世界毁灭。
灯突然亮了,门被打开。
一个高大的身形把我扶起,又将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。
他俯身低眸,给我检查额头的伤口。
清澈的声音,如细雨般洒落:
“赛场上的小豹子,哭肿眼睛就不好看了。”
我这才认出,他是入学时上台讲话的大学霸,隔壁班的理科天才许以琛。
不仅成绩优异,还是白净帅气的校草。
架一副银色边框眼镜,相当蛊人。
听说追他的女生都排到海边了。
但他对谁都很冷淡,拒之千里,已经把学校的多位美女弄哭。
搭眼一看,他的肤色白得透亮,身躯过于瘦削,呈现一种病态的美。
许以琛竟然认识我?
也是,表白墙上被全校嘲讽的女汉子,早就“名噪一时”。
“她长得好黑啊,祖籍非洲?”
“打拳好凶,女孩子为什么要学这种运动?”
“哪个男生敢靠近她?一个拳头抡过来,半条小命都没了。”
“五官长得倒精致,光看脸就是咖色小公主,脖子以下太虐,一位女壮士。”
他们肆意品评我的长相身材,周围充满黑色空气。
因为与大多数白幼瘦女孩不一样,班花谢紫萱便明目张胆带头孤立我。
别人投来的恶意,让我呼吸都无法顺畅。
我也在潜意识里认同,自己是一个丑陋的怪胎。
连父亲都讨厌我。
或许,我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。
许以琛用碘伏和棉签为我的伤口消毒,又轻轻贴上创可贴。
即使他把我送回家,我也只是低头啜泣,连一句谢谢都没说。
他是耀眼的星辰,而我是土里的石头。
因为一次顺手的助人为乐,幻想他对我与众不同,就太愚蠢了。
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。
第二天放学后,许以琛却在教室门口拦住我:
“我想邀请你当交谊舞比赛的舞伴?”
啊?
禁欲系男神,竟然邀请我,做他的舞伴?
一瞬间,我的脑子里似有烟花绽放。
把理智都炸得四分五裂。
我低下头,双手止不住揉搓,不知所措。
一旁的谢紫萱气得眼斜嘴歪,她摔包怒吼:
“以琛,你竟然为了她拒绝我?头脑简单的学渣,她不配。”
许以琛仿佛没听见,他直愣愣看着我,耳尖染上一层薄红。
我抬头对上他的眼睛,那温柔带笑的眸子,似幽深静谧的清潭。
心跳漏了一拍,头也一阵眩晕。
回过神时,我已经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:
“好啊,我可得过拉丁舞冠军呢。”
许以琛的眼睛顿时一亮,嘴角的笑满溢出来。
只一秒,他恢复到日常的冰冷,不动声色道:
“那还犹豫什么,现在去练习,我可是要得冠军的。”
众目睽睽下,许以琛拉着我的手离开。
身后,谢紫萱颤声威胁:“你们等着瞧,我一定会报仇。”
许以琛,到底为什么啊,何必为了我,得罪谢紫萱呢?
她可是校长的女儿。
6
那天傍晚,我在废弃楼的原音乐教室教他动作。
学霸果然聪明,许以琛学得很快,一点就通。
我接连教了他好几个动作,他跳得很标准。
但刚过了半个小时,他额头的汗涔涔落下,刘海的乱发紧贴在惨白的皮肤上。
他邀我到阶梯去休息,弯腰把叠好的外套放在地上。
我呆呆站立,却听他悠悠道:“坐,女孩子不能着凉的。”
面冷心细,原来他是这样的许以琛啊。
第二天课间操,我被谢紫萱和她的两个跟班堵在厕所里。
“丑八怪,谁让你逞能,以琛有先心病,他不能做剧烈运动。”
“以琛请假住院了,扫把星,你以后离他远点。”
谢紫萱太过激动,她竟然抬手,想去扯我的马尾。
我一个反手,差点把她的细胳膊掰断。
谢紫萱嚎叫着,小跟班连声求饶。
回教室的路上,我的脑海里浮现许以琛煞白的脸。
忽然联想到,有一次被欺负后,我跑到天台上抹眼泪,坐在墙角戴帽子睡觉的人就是他。
许以琛从来不上体育课。
我闯了大祸,在学校里唯一接近朋友的人差点被我害死。
我怎么那么笨,他都那么难受了,还看不出来。
好恨自己的粗心和愚蠢。
许以琛返校那天,我的转学申请刚好批下来。
放学后,我不想回家,坐在天台上看夕阳。
父亲要再婚了,娶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,叫妈是不是不合适?
我苦笑着,不管走到哪,我好像都是多余的人。
最后一抹晚霞消散时,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:
“赛场上的小豹子,遇事就逃避,算什么?”
“被舞伴单方面抛弃,好伤心。”
“这位同学,不会歧视先心病人吧?”